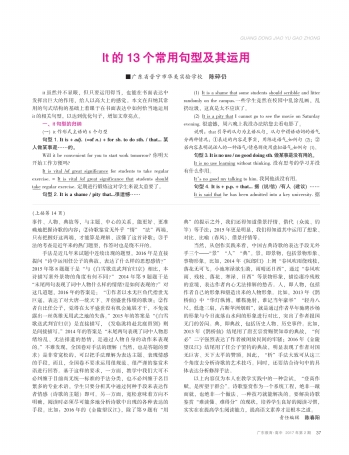手法是近几年来试题中连续出现的题型,2016年是直接提问“诗中运用任公子的典故,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2015年第8题题干是“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相比,本诗描写塞外景物的角度有何不同?” 2014年第9题题干是“末尾两句表现了词中人物什么样的情绪?是如何表现的?”对这几道题,2016年的答案是:“①作者以水无巨鱼代指世无巨寇,表达了对大唐一统天下、开创盛世伟绩的歌颂;②作者自比任公子,觉得在太平盛世没有机会施展才干,不免流露出一丝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2015年的答案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直接描写,《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则是间接描写。”2014年的答案是“末尾两句表现了词中人物思绪纷乱、无法排遣的愁情,是通过人物自身的动作来表现的。”不难发现,全国卷对手法的理解(当然,也是答题的要求)是非常宽松的,可以把手法理解为表达主题、表现情感的手段,而且,全国卷不要求运用很规范、很严谨的鉴赏术语进行回答。基于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教学中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于目前尚无统一标准的手法分类,也不必纠缠于名目繁多的专业术语,学生只要分析其中通过何种手段来表达作者情感(诗歌的主题)即可。另一方面,宽松意味着方向不明确,阅读时必须尽可能多地分析诗歌中出现的各种表达的手段。比如:2016年的《金陵望汉江》,除了第9题有“用典”的提示之外,我们还得知道借景抒情、借代(众流、钓竿)等手法;2015年更是明显,我们得知道其中运用了想象、对比、比喻(春风)、借景抒情等。
当然,从创作实践来看,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达手段无外乎三个——“景”“人”“典”。景,即景物,包括景物形象、事物形象。比如,2014年《阮郎归》上阕“春风吹雨绕残枝,落花无可飞。小池寒渌欲生漪,雨晴还日西”,通过“春风吹雨、残枝、落花、寒渌、日西”等景物形象,描绘凄冷残败的意境,表达作者内心无法排解的愁苦。人,即人物,包括作者自己的形象和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比如,2013年《鹊桥仙》中“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就是通过作者早年驰骋沙场的形象与今日流落山水间的形象进行对比,突出了作者报国无门的苦闷。典,即典故,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比如,2013年《鹊桥仙》结尾用了唐玄宗赏赐贺知章的典故,“何必”二字强烈表达了作者被闲放民间的牢骚;2016年《金陵望汉江》结尾用了任公子罢钓的典故,明显表现了作者对国无巨害、天下太平的赞颂。因此,“析”手法大致可从这三个角度去分析诗歌的艺术技巧。同时,还要结合诗句中的具体表达分析修辞手法。
以上内容仅为本人在教学实践中的一种尝试,“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诗歌鉴赏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也绝非一个做法、一种技巧就能解决的。要解决诗歌鉴赏“难读懂、难得分”的现状,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实实在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提高语文素养才是根本之道。
责任编辑 陈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