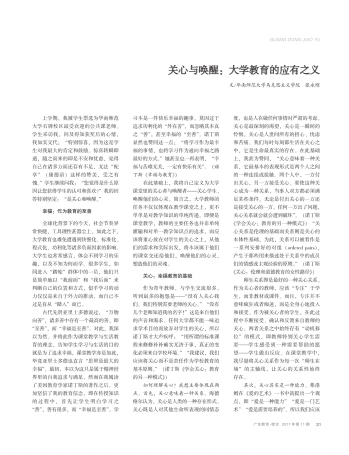上学期,我被学生票选为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最受欢迎的公共课老师。学生采访我,问及得知获奖后的心情,我如实交代:“特别惊喜,因为这是学生对我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惊喜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即是不安和忧虑,觉得自己在诸多方面还存有不足,无法“配享”(康德语)这样的赞美,受之有愧。”学生继续问我:“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获得学生的认可和喜欢?”我的回答特别坚定:“是关心和唤醒。”
幸福:作为教育的至善
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社会节奏异常快捷,工具理性甚嚣尘上。如此之下,大学教育也难免遭遇到快餐化、标准化、程式化、功利化等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也常常感言,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以及不知为何而学。很多学生,如同进入“踏轮”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只是简单地以“我前面”和“我后面”来判断自己的位置和方式,似乎学习的动力仅仅是来自于外力的推动,而自己不过是盲从“踏入”而已。
古代先贤亚里士多德说过,“万物向善”,诸多善中存有一个最高的善,即“至善”,而“幸福是至善”。对此,我深以为然。并将此作为课堂教学与生活教育的理念,告知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课堂教学亦是如此,毕竟亚里士多德也直言“思辨是最大的幸福”。最初,本以为这只是属于精神世界里的自我追求与满足,然而在我阅读了美国教育学家诺丁斯的著作之后,更加坚信了我的教育信念,即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首先让学生明白学习之“善”,善有很多,而“幸福是至善”。学习本是一件快乐幸福的趣事,莫因过于追求功利化的“外在善”,而忽略其本真之“善”,甚至幸福的“至善”。诺丁斯显然也赞同这一点:“将学习作为最幸福的事情,也将学习作为通向幸福之路最好的方式。”她甚至也一再表明,“幸福与苦难无关,一定有快乐有关”。(诺丁斯《幸福与教育》)
在此基础上,我将自己定义为大学课堂里的关心者与唤醒者——关心学生、唤醒他们的心灵。简言之,大学教师的任务不仅仅体现在教学课堂之上,更不单单是对教学知识的单纯传递。即便是课堂教学,教师的主要任务也并非单纯灌输和对单一教学知识点的追求,而应该将重心放在对学生的关心之上,从他们的需求和实际出发,将本该属于他们的课堂交还给他们,唤醒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的灵魂。
关心:幸福教育的基础
作为青年教师,与学生交流很多,听到最多的抱怨是——“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特别需要老师的关心。”“没有几个老师知道我的名字!”这是来自他们的声音和渴求。任何大学都不能一味追求学术目的而放弃对学生的关心,所以诺丁斯才大声疾呼:“用所谓的标准课程来修修补补确实无济于事,真正的变化必须来自学校环境。”“我建议,我们应该将关心而不是责任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如何理解关心?我想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关心意味着一种关系。海德格尔认为,关心是人类的一种存在形式。关心既是人对其他生命所表现的同情态度,也是人在做任何事情时严肃的考虑。关心是最深刻的渴望,关心是一瞬间的怜悯,关心是人世间所有的担心、忧虑和苦痛。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关心之中,它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甚为赞同,“关心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或接触。两个人中,一方付出关心,另一方接受关心。要使这种关心成为一种关系,当事人双方都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无论是付出关心的一方还是接受关心的一方,任何一方出了问题,关心关系就会就会遭到破坏”。(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关心关系是伦理的基础而关系则是关心的本体性基础。为此,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安排好的对组(ordered pairs),产生于那些用来描述处于关系中的成员们的情感或主观经验的原则。”(诺丁斯《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路径》)
师生关系即是最好的一种关心关系。作为关心者的教师,应该“专注”于学生,而非教材或课件。而且,专注并不意味疯狂或者痴迷,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和接受。作为被关心者的学生,在此过程中不断接受、确认和反馈来自教师的关心。两者关系之中始终存有“动机移位”的模式,即教师特别关心学生需要——学生感受到一种需要帮助的愿望——学生做出反应。在课堂教学中,我尽量将关心关系作为每一次“师生在场”的主轴线,让关心的关系性始终存在。
其次,关心其实是一种能力。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就提出一个观点,即“爱是一种能力”“爱是一门艺术”“爱是需要培养的”。所以我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