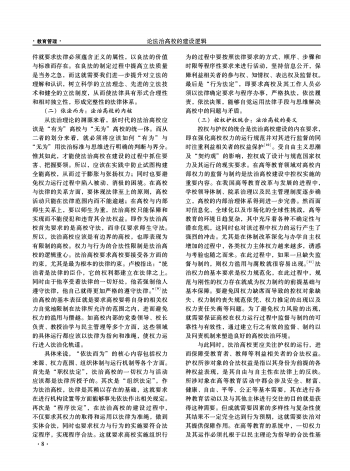(二)依法而为:法治高校的内核
从法治理论的渊源来看,新时代的法治高校应该是“有为”高校与“无为”高校的统一体。而从二者的划分来看,就必须将应该如何“有为”与“无为”用法治标准与思维进行明确的判断与界分。惟其如此,才能使法治高校在建设的过程中抓住要害、把握要领。所以,应该在实践中防止试图构建全能高校,从而过于膨胀与张扬权力;同时也要避免权力运行过程中陷入被动、消极的困境。在高校与法律的关系方面,要体现法律至上的原则,高校活动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而不能逾越;在高校与内部师生关系上,要以师生为重,法治高校只能保障和实现而不能侵犯和违背其合法权益。即作为法治高校首先要求的是高校守法,而非仅要求师生守法。所以,法治高校应该是有边界的高校,也即表现为有限制的高校。权力与行为的合法性限制是法治高校的逻辑重心。法治高校要求高校要接受各方面的约束,尤其是最为根本的法律约束。卢梭指出:“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它的权利都建立在法律之上。同时由于他享受着法律的一切好处,他若强制他人遵守法律,他自己就得更加严格的遵守法律。”[9]法治高校的基本表征就是要求高校要将自身的相关权力自觉地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而避免权力的滥用与僭越。如高校内部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与民主管理等多个方面,这些领域的具体运行都应该以法律为指向和准绳,使权力运行进入法治化轨道。
具体来说,“依法而为”的核心内容包括权力来源、权力范围、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首先是“职权法定”,法治高校的一切权力与活动应该都是法律所授予的。其次是“组织法定”,作为法治高校,法律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要求在进行机构设置等方面能够事先依法作出相关规定。再次是“程序法定”,在法治高校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求其权力的取得和运用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实体合法,同时也要求权力与行为的实施要符合法定程序,实现程序合法。这就要求高校实施组织行为的过程中要按照法律要求的方式、顺序、步骤和时限等程序性要求来进行活动,坚持信息公开,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及监督权。最后是“行为法定”,即要求高校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以法律确定要求与程序办事,严格执法,依法履责,依法决策,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手段与思维解决高校中的问题与矛盾。
(三)控权护权统合:法治高校的要义
控权与护权的统合是法治高校建设的内在要求,即在强化高校权力的运行规范并对其进行监督的同时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10]。受自由主义思潮及“契约观”的影响,控权成了设计与规范国家权力及其运行的现实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对高校内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法治高校建设中控权实施的重要内容。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学校领导体制、院系治理以及民主管理制度逐步确立,高校的内部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然而面对信息化、全球化以及市场化的全球性挑战,高等教育的环境日趋复杂,其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与潜在危机,这同时也对该过程中权力的运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尤其是在体制改革深化与办学自主权增加的过程中,各类权力主体权力越来越多,诱惑与考验也随之而来。在此过程中,如果一旦缺失监督与制约,则权力滥用与腐败就很容易出现。[11]法治权力的基本要求是权力规范化,在此过程中,规范与刚性的权力存在就成为权力制约的前提基础与基本保障。要避免因权力缺席而导致的控权对象缺失、权力制约丧失规范依凭、权力推定的出现以及权力责任失衡等问题。为了避免权力风险的出现,就需要保证高校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监督与制约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以及问责机制来塑造良好的高校法治环境。
与此同时,法治高校更应关注护权的运行,进而保障受教育者、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护权所涉对象的合法权益是指以其身份为前提的各种权益表现,是其自由与自主性在法律上的反映。所涉对象在高等教育活动中都会涉及安全、财富、健康、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需要,其在进行各种教育活动以及与其他主体进行交往的目的就是获得这种需要。但成就需要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其结果不一定完全达到行为预期,这就需要法治对其提供保障作用。在高等教育的系统中,一切权力及其运作必须扎根于以民主理论为指导的合法性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