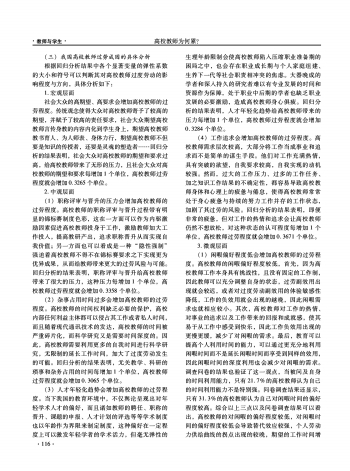根据回归分析结果中各个显著变量的弹性系数的大小和符号可以判断其对高校教师过度劳动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具体分析如下:
1.宏观层面
社会大众的高期望、高要求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传统观念使得大众对高校教师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并赋予了较高的责任要求,社会大众期望高校教师言传身教的内容内化到学生身上,期望高校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期望高校教师不但要是知识的传授者,还要是灵魂的塑造者……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大众对高校教师的期望和要求过高,给高校教师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且社会大众对高校教师的期望和要求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3265个单位。
2.中观层面
(1)职称评审与晋升的压力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与晋升过程带有明显的锦标赛制度色彩,这在一方面可以作为内驱激励因素促进高校教师投身于工作,激励教师加大工作投入,提高教研产出,追求职称晋升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隐性强制”强迫着高校教师不得不在锦标赛要求之下实现更为优异成果,从而给教师带来更大的过劳风险与可能。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职称评审与晋升给高校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3358个单位。
(2)杂事占用时间过多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高校教师的时间权利缺乏必要的保护,高校内部任何利益主体都可以侵占其工作或者私人时间,而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高校教师的时间被严重碎片化,而科学研究又是需要时间深度的。因此,高校教师需要利用更多的自我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无限制的延长工作时间,加大了过度劳动发生的可能。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无关教学、科研的琐事和杂务占用的时间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3065个单位。
(3)人才年轻化趋势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当下我国的教育环境中,不仅舆论呈现出对年轻学术人才的偏好,而且诸如教师的聘任、职称的晋升、课题的申报、人才计划的评选等等学术制度也以年龄作为界限来制定制度,这种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年轻学者的学术活力,但毫无弹性的生理年龄限制会使高校教师陷入压缩职业准备期的困局之中,也会存在职业成长期与个人家庭组建、生养下一代等社会职责相冲突的焦虑。大器晚成的学者和深入持久的研究者难以有专业发展的时间和资源作为保障,处于职业中后期的学者也缺乏职业发展的必要激励,造成高校教师身心俱疲。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才年轻化趋势给高校教师带来的压力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3284个单位。
(4)工作追求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高校教师需求层次较高,大部分将工作当成事业和追求而不是简单的谋生手段。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具有突破的欲望,自我要求较高,自我实现的动机较强。然而,过大的工作压力、过多的工作任务、加之知识工作结果的不确定性,都容易导致高校教师身体和心理上的疲惫与倦怠,使得高校教师常常处于身心疲惫与持续的努力工作并存的工作状态,加剧了其过劳的风险。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即便非常的疲惫,但对工作的热情和追求会让高校教师仍然不想放松,对这种状态的认可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3671个单位。
3.微观层面
(1)闲暇偏好程度低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高校教师的闲暇偏好程度较低,首先,因为高校教师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制,因此教师可以充分调整自身的状态,过劳副效用出现就会较迟,或者对过度劳动副效用的体验敏感性降低,工作的负效用就会出现的越晚,因此闲暇需求也就相应较小。其次,高校教师对工作的热情、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工作带来的回报和成就感,使其易于从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因此工作负效用出现的更慢更缓,减少了对闲暇的需求。最后,教育可以提高个人利用时间的能力,可以通过更充分地利用闲暇时间而不是延长闲暇时间而享受到同样的效用,因此闲暇时间的深度利用也会减少对闲暇的需求。调查问卷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当被问及自身的时间利用能力,只有21.7%的高校教师认为自己的时间利用能力不是特别强。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只有31.3%的高校教师认为自己对闲暇时间的偏好程度较高。综合以上三点以及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对闲暇的偏好程度较低,对闲暇时间的偏好程度较低会导致替代效应较强,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拐点出现的较晚,期望的工作时间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