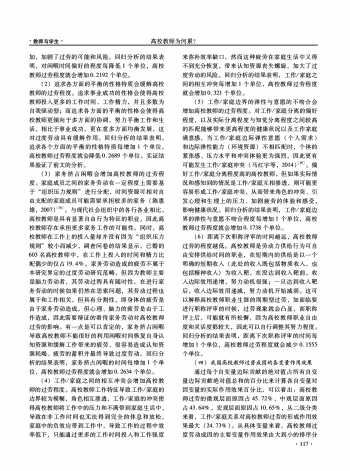(2)追求各方面的平衡的性格特质会缓解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追求事业成功的性格会使得高校教师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工作精力,并且多数为自我驱动型;而追求各方面的平衡的性格会使得高校教师更倾向于多方面的协调,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相比于事业成功,更在意多方面均衡发展,这对过度劳动具有缓解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追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的性格特质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降低0.2689个单位。实证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分析。
(3)家务挤占闲暇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家庭成员之间的家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基于“组织压力规则”进行分配,时间资源可相对自由支配的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承担较多的家务(陈惠雄,2007)[18]。与现代社会组织中的各行各业相比,高校教师是具有显著自由行为特征的职业,因此高校教师存在承担更多家务工作的可能性。同时,高校教师在工作上的投入量却并没有因为“组织压力规则”较小而减少,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已婚的603名高校教师中,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配偶少的仅占19.4%。家务劳动造成的疲劳不属于本研究界定的过度劳动研究范畴,但因为教师主要是脑力劳动者,其劳动过程具有随时性,在进行家务劳动的时候如果仍然在思索问题,其劳动过程也属于和工作相关,但具有分割性,即身体的疲劳是由于家务劳动造成,但心理、脑力的疲劳是由于工作造成,因此需要辩证的看待家务劳动对高校教师过劳的影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家务挤占闲暇导致高校教师不能很好的利用闲暇时间恢复自身认知资源和缓解工作带来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认知资源耗竭、疲劳的蓄积并最终导致过度劳动。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务挤占闲暇的时间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2634个单位。
(4)工作/家庭之间的相互冲突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高校教师工作特征导致工作/家庭的边界较为模糊,角色相互渗透,工作/家庭的冲突使得高校教师将工作中的压力和不满带到家庭生活中,导致在非工作时间也无法得到完全的休息和放松,家庭中的负效应带到工作中,导致工作的过程中效率低下,只能通过更多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作强度来弥补效率缺口,然而这种疲劳在家庭生活中又得不到充分恢复,带来认知资源丧失螺旋,加大了过度劳动的风险。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作/家庭之间的相互冲突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321个单位。
(5)工作/家庭边界的弹性与意愿的不吻合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过劳程度。对工作/家庭分离的偏好程度,以及实际分离程度与知觉分离程度之间较高的匹配能够带来更高程度的健康状况以及工作家庭满意感,当工作/家庭边际弹性意愿(个人需求)和边际弹性能力(环境资源)不相匹配时,个体的紧张感、压力水平和冲突体验更为强烈,因此更有可能发生工作/家庭冲突(马红宇等,2014)[19]。偏好工作/家庭分离程度高的高校教师,但如果实际情况和感知到的情况是工作/家庭互相渗透,则可能更容易形成工作/家庭冲突,从而带来角色的冲突、引发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加剧疲劳的体验和感受,影响健康状况。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作/家庭边界的弹性与意愿不吻合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增加0.1738个单位。
(6)距离下次职称评审的时间越远,高校教师过劳的程度越低。高校教师是劳动力供给行为可自由安排供给时间的职业,在短期内的供给是以一个明确的短期收入(此处的收入既包括物质收入,也包括精神收入)为收入靶,在没达到收入靶前,收入边际效用递增,努力动机很强;一旦达到收入靶后,收入边际效用递减,努力动机开始减弱。这可以解释高校教师职业生涯的周期型过劳,如面临要进行职称评审的时候,过劳现象就会凸显,而职称评上后,可能就有所松懈,因为高校教师职业自由度和灵活度都较大,因此可以自行调整其努力程度。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距离下次职称评审的时间每增加1个单位,高校教师过劳程度就会减少0.1555个单位。
(四)我国高校教师过劳成因的各变量作用效果
通过每个自变量边际贡献的绝对值占所有自变量边际贡献绝对值总和的百分比来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实际作用效果百分比,可以看出:高校教师过劳的微观层面原因占45.72%,中观层面原因占43.64%,宏观层面原因占10.65%,从二级分类来看,工作/家庭关系对高校教师过劳的形成作用效果最大(24.73%)。从具体变量来看,高校教师过度劳动成因的主要变量作用效果由大到小的排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