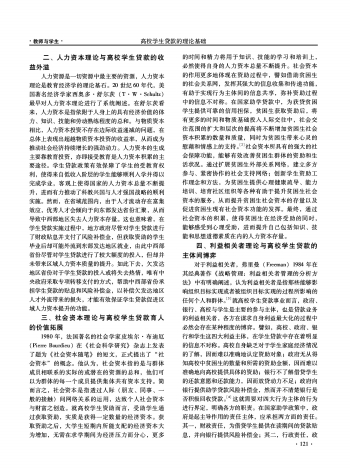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石。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最早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于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总和。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投资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在总体上表现出超越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从而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人力资本的生成主要靠教育投资,亦即接受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学生贷款政策有效保障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使得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并得以完成学业,客观上使得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不断提升,进而有力推动了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然而,在省域范围内,由于人才流动存在富集效应,优秀人才会倾向于向东部发达省份汇聚,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失去人力资本存量。这也意味着,在学生贷款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尽管对学生贷款进行了财政贴息并支付了风险补偿金,但获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却可能外流到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由此中西部省份尽管对学生贷款进行了较大额度的投入,但却并未带来区域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如此下去,欠发达地区省份对于学生贷款的投入或将失去热情,唯有中央政府采取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中西部省份承担学生贷款的贴息和风险补偿金,以补偿欠发达地区人才外流带来的损失,才能有效保证学生贷款促进区域人力资本提升的功能。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育人的价值拓展
1980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他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简而言之,社会资本是指透过人际(朋友、同事、一般的接触)间网络关系的运用,达致个人社会资本与财富之创造。就高校学生资助而言,受助学生通过获取资助,实质是获得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获取资助之后,大学生短期内所能支配的经济资本大为增加,无需在求学期间为经济压力而分心,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将用于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培训上,必然使得自身的人力资本总量不断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资助过程中,譬如借助贫困生的社会关系网,发挥其强大的信息收集和传递功能,有助于实现行为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弥补资助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国家助学贷款中,为获贷贫困学生提供可靠的信用担保,贫困生获取资助后,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物质基础投入人际交往中,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将不断增加贫困生社会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为贫困生带来心灵的慰藉和情感上的支持。[2]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能够有效改善贫困生群体的资助和生活状况。通过扩展贫困生外部关系网络,建立多方参与、紧密协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创新学生资助工作理念和方法,为贫困生提供心理健康疏导、能力培训、培育社区组织等各种有助于提升贫困生社会资本的服务,从而提升贫困生社会资本的存量以及促进贫困生现有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最终,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贫困生在经济受助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心理受助,进而提升自己包括知识、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人力资本存量。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主体间博弈
对于利益相关者,弗里曼(Freeman)1984年在其经典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有明确阐述,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被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3]就高校学生贷款事业而言,政府、银行、高校与学生是主要的参与主体,也是贷款业务的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博弈。譬如,高校、政府、银行和学生这四大利益主体,在学生贷款中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高校自身缺乏对于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了解,因而难以准确地认定资助对象;政府无从得知高校中贫困生的数量和所需的资助金额,因而难以准确地向高校提供具体的资助;银行不了解借贷学生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因而放贷动力不足;政府向银行提供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然而并不清楚银行是否积极回收贷款。[4]这就需要对四大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界定,明确各方的职责。在国家助学政策中,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责任主体,应承担两方面的责任。其一,财政责任,为借贷学生提供在读期间的贷款贴息,并向银行提供风险补偿金;其二,行政责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