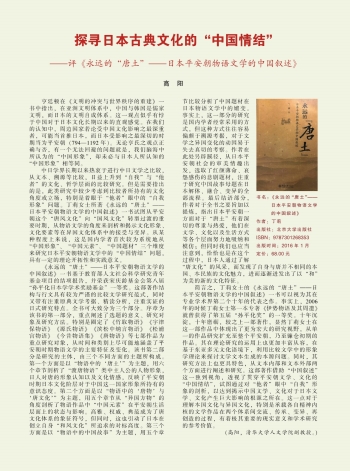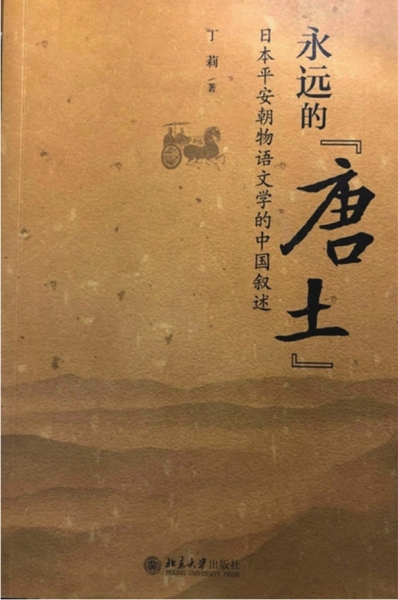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在亚洲文明体系中,中国与韩国是儒家文明,而日本的文明自成体系。这一观点似乎有悖于中国对于日本文化长期以来的直观感觉。在我们的认知中,周边国家若论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最深重者,可能当首推日本,而日本受影响之最深切的时期当为平安朝(794—1192年)。无论亨氏之观点正确与否,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脑海中所认为的“中国形象”,却未必与日本人所认知的“中国形象”相等同。
中日学界长期以来热衷于进行中日文学之比较,从文本、溯源等比较,日益上升到“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哲学层面的比较研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中较少考虑到比较者所持有的文化角度或立场,特别是着眼于“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问题。丁莉女士所著《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一书试图从平安朝这个“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从物语文学的角度来剖析和揭示文化形象、文化要素等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的接受与变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国内学者首次较为系统地从“中国形象”、“中国元素”、“中国题材”三个维度来研究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中的“中国情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开拓性和实践意义。
《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一书基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结项报告,并荣获宋庆龄基金会第八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一等奖。这部著作结构与行文具有较为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同时又带有注重原典文学考据、精读分析,注重实证的日式研究特点。全书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序章为该书的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选题的意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特别是圈定了《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松浦宫物语》《今昔物语集》《唐物语》等七部作品为重点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类别上尽可能地涵盖了平安朝时期物语文学的主要特征及变化。该书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体,由三个不同方面的主题所构成。第一个方面是以“物语中的‘唐土’”为主题,用六个章节剖析了“渡唐物语”类中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日人对唐的形象认知以及文化情感,反映了平安朝时期日本文化阶层对于中国这一国家形象所持有的意识态度。第二个方面是以“物语中的‘唐物’与‘唐文化’”为主题,用五个章节从“异国方物”的角度剖析了物语作品中“中国元素”在平安朝生活层面上的状态与影响。高雅、权威、典范成为了唐文化体系的象征符号,但同时,这也引动了日本在创立自身“和风文化”所追求的对标高度。第三个方面是以“物语中的中国故事”为主题,用五个章节比较分析了中国题材在日本物语文学中的嬗变。事实上,这一部分的研究是国内学者经常采用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往往容易偏颇于溯源考据,对于文学之异国变化的动因易于失去真切的考察。作者在此处另辟蹊径,从日本平安朝社会的审美情趣出发,选取了红颜薄命、哀怨感伤的悲剧题材,注重于研究中国故事母题在日本解体、融合、变异的全部流程。最后结语部分,作者对于全书之要旨加以提炼,指出日本平安朝一方面对于“唐土”有着深切的尊重与热爱,他们在文学、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努力地吸纳和模仿;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恰恰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通过了解“唐文化”的风采,而发现了自身与唐并不相同的本国、本民族的文化魅力,进而逐渐迸发出了以“和”为美的新的文化特征。
简言之,丁莉女士的《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一书可以视为其在专业学术界第二个十年的代表之作。事实上,2006年的时候丁莉女士第一本专著《伊势物语及其周遭》就曾获得了第五届“孙平化奖”的一等奖。十年沉淀,十年磨砺,较之上一部著作,显然丁莉女士在这一部作品中体现出了更为宏大的研究视野,从单一的作品研究扩充至整个平安朝,乃至镰仓初期的作品。其在理论研究的运用上也更加丰富从容,在基于东亚多元文化语境下,利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来探讨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问题。同时,其研究方法上也更具特色,从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研究。这部著作借助“中国叙述”这一独到视角,透视了贯穿平安朝文学、文化的“中国情结”,试图通过对“他者”眼中“自我”形象的剖析,以达到揭示中国文学、文化对于日本文学、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源之所在。这一点对于理解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特别是承载各自精神内核的文学作品在两个体系间交流、传承、变异、再创造的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
(高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