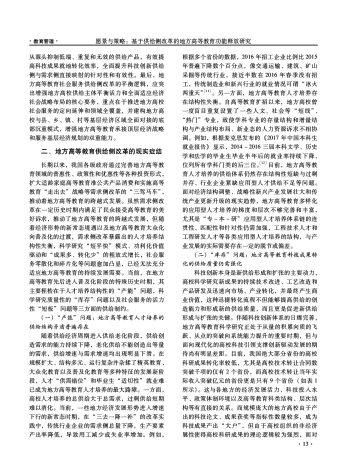二、地方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现实症结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通过完善地方高等教育领域的普惠性、政策性和优惠性等各种投资形式,扩大适龄家庭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消费和实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等需求侧改革的“三驾马车”,推动着地方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虽然需求侧改革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满足了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好诉求,推动了地方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新常态境遇以及地方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过渡,需求侧改革暴露出的人才培养结构性失衡,科学研究“短平快”模式、功利化价值驱动和“成果多、转化少”的粗放式增长,社会服务零散化和碎片化等问题愈加凸显,已经无法充分适应地方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需要。当前,在地方高等教育先后进入普及化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其主要桎梏在于人才培养结构性的“产能”问题,科学研究质量性的“库存”问题以及社会服务的活力性“短板”问题等三方面的供给制约。
(一)“产能”问题:地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结构矛盾普遍存在
随着供给经济周期进入供给老化阶段,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持续下降,老化供给不能创造出等量的需求,供给增速与需求增速均出现明显下滑。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并杂揉了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以及普及化教育等多种特征的发展新阶段,人才“供需错位”和毕业生“适切性”就业难已成为地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大路障。一方面,高校人才培养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形势进入增速下行的新常态时期,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实践中,传统行业企业的需求侧总量下降,生产要素产出率降低,导致用工减少或失业率增加。例如,根据多个省份的数据,2016年招工企业比例比2015年普遍下降数个百分点,像交通运输、建筑、矿山采掘等传统行业,接近半数在2016年春季没有招工,传统制造业和新兴行业的就业情况可谓“冰火两重天”[11]。另一方面,地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失衡。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地方高校曾一度盲目重复设置了一些人文、社会等“短线”、“热门”专业,致使学科专业的存量结构和增量结构与产业结构布局、新业态的人力资源诉求不相协调。例如,根据麦克思发布的《2017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14-2016三届本科文学、历史学和法学的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持续下降,位列所有学科门类的后三位。[12]目前,地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体系仍然存在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行业企业紧缺应用型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面对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传统产业更新升级的现实趋势,地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梯度和层次不够完善和丰富,尤其是“专-本-研”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链的连贯性、匹配性和针对性仍需加强,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研发人才等各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结构,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存在一定的脱节或偏差。
(二)“库存”问题:地方高等教育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质量仍需强化
科技创新本身是新供给形成和扩张的主要动力,高校科学研究新成果的持续技术改进、工艺改造和产品研发及迅速向市场、产业转化,并最终产生商业价值,这种迅捷转化流程不但能够提高供给的创造能力和形成新的供给质量,而且更是促进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关键。伴随科技创新体系的日臻完善,地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但与面向现代化的高校科技引领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期待尚有明显差距。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尤其是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突破千项的仅有2个省份,而高校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突破亿元的省份更是只有9个省份(如表1所示)。这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活力、科技投入水平、政策体制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层次结构等有直接的关系。而规模庞大的地方高校由于产出的科技论文、成果获奖等指标性数量较多,成为科技成果产出“大户”,但由于高校组织的非经济属性使得高校科研成果的理论逻辑较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