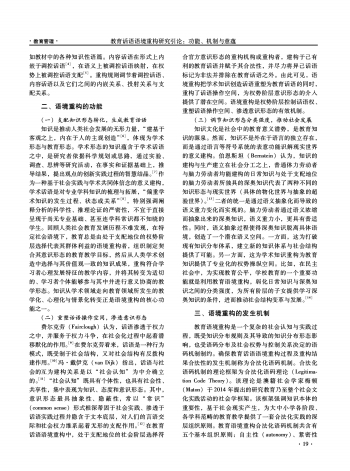二、语境重构的功能
(一)支配知识形态转化,生成教育话语
知识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建基于客观之上,内在于人的主观创造”[6],体现为学术形态与教育形态。学术形态的知识蕴含于学术话语之中,是研究者依据科学规划或思路,通过实验、调查、思辨等研究活动,在事实和证据基础上,推导结果,提出观点的创新实践过程的智慧结晶。[7]作为一种基于社会实践与学术共同体信念的意义建构,学术话语是对专业学科知识的梳理与拓展,“偏重学术知识的发生过程、状态或关系”[8],特别强调阐释分析的科学性、推理论证的严密性,不宜于直接呈现于尚无专业基础、甚至连学科常识都不知晓的学生。回顾人类社会教育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特定社会语境下,教育总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势阶层选择代表其群体利益的语境重构者,组织制定契合其意识形态的教育教学目标,然后从人类学术创造中选择与其价值观一致的知识成果,重构符合学习者心理发展特征的教学内容,并将其转变为适切的、学习者个体能够参与其中并进行意义协商的教学形态。知识从学术领域走向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学化、心理化与情景化转变正是语境重构的核心功能之一。
(二)重塑话语操作空间,渗透意识形态
费尔克劳(Fairclough)认为,话语渗透于权力之中,并服务于权力斗争,在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9]在费尔克劳看来,话语是一种行为模式,既受制于社会结构,又对社会结构有反拨构建作用。[10]冯·戴伊克(van Dijk)指出,话语与社会的互为建构关系是以“社会认知”为中介确立的。[11]“社会认知”既具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共享性,集中表现为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最具抽象性、隐蔽性,常以“常识”(common sense)形式根深蒂固于社会实践、渗透于话语实践过程并隐含于文本底层,对人们的言语交际和社会权力维系起着无形的支配作用。[12]在教育话语语境重构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选择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重构机构或重构者,建构于己有利的教育话语并赋予其合法性,并尽力将异己话语标记为非法并排除在教育话语之外。由此可见,语境重构把学术知识创造话语重塑为教育话语的同时,重构了话语操作空间,为权势阶层意识形态的介入提供了潜在空间。语境重构是权势阶层控制话语权、重塑话语操作空间、渗透意识形态的有效机制。
(三)调节知识形态分类强度,推动社会发展
知识文化是社会中的教育意义潜势,是教育知识的源泉。然而,知识不是外在于语言的独立存在,而是通过语言等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识解现实世界的意义建构。伯恩斯坦(Bernstein)认为,知识的建构与生产建立在社会分工之上,普通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均能建构的日常知识与处于支配地位的脑力劳动者所独具的深奥知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与现实世界(具体的物化世界与抽象的超验世界)。[13]二者的统一是通过语义抽象化而导致的语义重力变化而实现的。脑力劳动者通过语义浓缩而抽象出来的深奥知识,语义重力小,更具有普适性。同时,语义抽象过程使得深奥知识脱离具体语境,创造了一个潜在语义空间。一方面,这为打破现有知识分布体系,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这为学术知识重构为教育知识提供了专业化的权势操纵空间。比如,在民主社会中,为实现教育公平,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利用教育语境重构,弱化日常知识与深奥知识之间的分类强度,为所有阶层的子女提供学习深奥知识的条件,进而推动社会结构变革与发展。[14]
三、语境重构的发生机制
教育语境重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认知与实践过程,既受知识分布规则及其导致的知识分布形态影响,也受语码分布及社会权势与控制关系决定的语码机制制约。确保教育话语语境重构过程及重构结果合法性的发生机制称为合法化语码机制。合法化语码机制的理论框架为合法化语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该理论是澳籍社会学家梅顿(Maton)于2014年提出的研究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的社会学框架。该框架强调知识本体的重要性,基于社会现实产生,为大中小学各阶段、各学科范畴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一套合法化实践的深层组织原则。教育语境重构合法化语码机制共含有五个基本组织原则:自主性(autonomy)、紧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