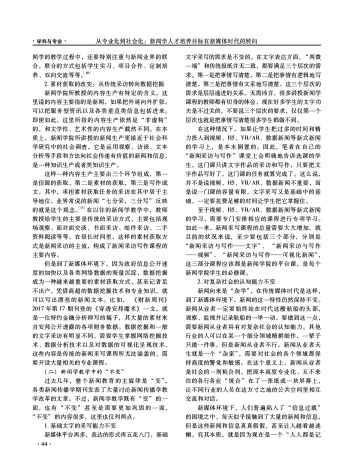2.素材获取的改变:从传统采访转向数据挖掘
新闻学院所教授的内容生产有特定的含义,这里说的内容主要指的是新闻,如果把外延向外扩张,可以把服务型资讯以及各类垂直类信息包括进来。即使如此,这里所指的内容生产依然是“非虚构”的,和文学性、艺术性的内容生产截然不同。在本质上,新闻学院所讲授的新闻生产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调查,它是运用观察、访谈、文本分析等手段和方法向社会传递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是一种知识生产或者类知识生产。
这样一种内容生产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第一是信源的获取,第二是素材的获取,第三是写作成文,其中,承担素材获取任务的采访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业界常说的新闻“七分采,三分写”反映的就是这个观念。[11]在以往的新闻学教学中,教师教授给学生的主要是传统的采访方式,主要包括现场观察、面对面交谈、书面采访、邮件采访、二手资料阅读等等。在很长时间里,这样的素材获取方式是新闻采访的主流,构成了新闻采访写作课程的主要内容。
但是到了新媒体环境下,因为政府信息公开速度的加快以及各类网络数据的海量沉淀,数据挖掘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素材获取方式,甚至记者足不出户,凭借高超的数据挖掘技术和专业知识,就可以写出漂亮的新闻文本。比如,《财新周刊》2017年第17期刊登的《穿透安邦魔术》一文,就是一位特约金融分析师写的稿子,其大量的素材来自安邦公开透露的各项财务数据。数据挖掘和一般的文字采访有明显不同,需要学生掌握网络挖掘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以及对数据的可视化呈现技术,这些内容是传统的新闻采写课程所无法涵盖的,需要开设大量相关的专业课程。
(二)新闻学教学中的“不变”
过去几年,整个新闻教育的主旋律是“变”,各类新闻传播学期刊发表了大量讨论新闻传播学教学改革的文章。不过,新闻学教学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甚至是需要更加巩固的一面,“不变”的内容很多,这里也仅列两点。
1.基础文字的采写能力不变
新媒体平台再多,表达的形式再五花八门,基础文字采写的需求是不变的。在文字表达方面,“两微一端”和传统报纸并无二致,都要满足三个层次的需求。第一是把事情写清楚,第二是把事情有逻辑地写清楚,第三是把事情有文采地写清楚,这三个层次的需求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无需讳言,很多讲授新闻学课程的教师都有切身的体会,现在好多学生的文字功夫是不过关的,不要说三个层次的要求,仅仅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把事情写清楚很多学生都做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学生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视频、H5、VR/AR、数据新闻等新式新闻的学习上,是本末倒置的。因此,笔者在自己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堂上会明确地告诉选课的学生,这门课只讲文字作品的采访和写作,只要把文字作品写好了,这门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么说,并不是说视频、H5、VR/AR、数据新闻不重要,而是说一门课的容量有限,文字采写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一定要花费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把它掌握住。
至于视频、H5、VR/AR、数据新闻等新式新闻的学习,需要专门安排相应的课程进行专项学习。如此一来,新闻采写课程的总量需要大大增加,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至少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新闻采访与写作——文字”、“新闻采访与写作——视频”、“新闻采访与写作——可视化新闻”,这三部分课程应该都是新闻学院的平台课,是每个新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2.对复杂社会的认知能力不变
新闻向来是“杂学”,在传统媒体时代是这样,到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的这一特性仍然保持不变。新闻从业者一定要始终站在时代这艘航船的头部,观察、监视并记录航船的一举一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新闻从业者具有对复杂社会的认知能力。其他行业的人可以在某一个细分领域精耕细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但是新闻从业者不行。新闻从业者天生就是一个“杂家”,需要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敏感。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一剂粘合剂,把原本高度专业化、互不来往的各行各业“统合”在了一张纸或一块屏幕上,让不同行业的人员在这方寸之地的公共空间里相互交流和对话。
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普遍陷入了“信息过载”的困境之中,每天似乎接触到了大量的新闻和信息,但是这些新闻和信息真真假假,甚至让人越看越迷糊,究其本质,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