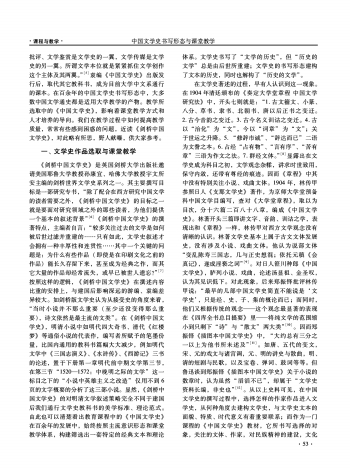一、 文学史作品选取与课堂教学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世界文学史系列之一。其主要撰写目标是一部研究专书,“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需要之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6]《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撰著特点,主编者自言:“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只有如此,文学史叙述才会拥有一种丰厚性和连贯性……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长久存留下来,甚至成为经典之作,而其它大量的作品却经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遗忘?”[7]按照这样的逻辑,《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撰述内容比重的安排上,与建国后影响深远的游编、袁编差异较大。如剑桥版文学史认为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诗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类”。在《剑桥中国文学史》,明清小说中如明代四大奇书、清代《红楼梦》等通俗小说的代表作,编写者所赋予的笔墨份量,比国内通用的教科书篇幅大大减少,例如明代文学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书的论述,置于下册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第三节,在第三节“1520—1572:中晚明之际的文学”这一标目之下的“小说中英雄主义之改造”仅用不到6页的文字概要的分析了这三部小说。显然,《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对明清文学叙述策略完全不同于建国后我们通行文学史教科书的美学标准、理论范式。由此也可以清楚看出教育课程中的《中国文学史》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始终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和课堂教学体系,构建筛选出一套特定的经典文本和理论体系。文学史书写了“文学的历史”,但“历史的文学”总是由后世所重建;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建构了文本的历史,同时也解构了“历史的文学”。
在文学史著述的过程,早有人认识到这一现象。在1904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 中国文学研究法》中,开头七则就是:“1.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2.古今音韵之变迁。3.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4.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5.“修辞市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誊之本。6.占经“占有物”、“言有序”、“苦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7.群经文体。”[8]显露出在文学史成为科目之初,文学观念杂糅,讲求时世致用,保守内敛,还带有尊经的痕迹。因而《章程》中其中没有特别关注小说、戏曲文体。1904年,林传甲参照日人《支那文学史》著作,为京师大学堂预备科中国文学目编写,查对《大学堂章程》,取以为目次,分十六篇二百八十八章,编成《中国文学史》。林著开头三篇即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表现出和《章程》一样,林传甲对西方文学观念没有清晰的认识。林著文学史基本上属于古文文体发展史,没有涉及小说、戏曲文体。他认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想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9]。对日人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胪列小说、戏曲,论述汤显祖、金圣叹,认为其见识低下。对此现象,后来郑振铎批评林传甲说:“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10]。因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为他书所未述及”[11]。如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但鲁迅谈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关于小说的数章时,认为虽然“滔滔不已”,却属于“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12]。从以上史料可见,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选择怎样的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从何种角度去建构文学史,与文学史文本的面貌、特质、时代意义有着重要联系;而作为一门课程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它所书写选择的对象,关注的文体、作家,对民族精神的建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