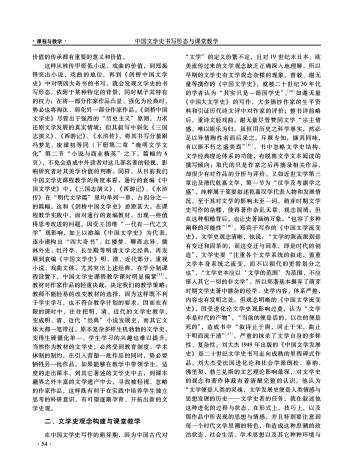这样从林传甲贬低小说、戏曲的价值,到郑振铎突出小说、戏曲的地位,再到《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对明四大奇书的书写,就会发现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依附于某种特定的背景,同时赋予其特有的权力;在将一部分作家作品凸显、强化为经典时,势必也将淘汰、弱化另一部分作家作品。《剑桥中国文学史》尽管出于强烈的“历史主义”原则,力求还原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境;但其叙写中弱化《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将其书写分量跟冯梦龙、凌濛初等同(下册第二章“晚明文学文化”第二节“小说与商业精英”之下,篇幅约 6页),不免会造成中外读者对这几部名著的轻视,影响研究者对其美学价值的判断。同样,从目前我们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的角度来看,通行的袁编《中国文学史》中,《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在“明代文学篇”里均单列一章,占四分之一的篇幅,这和《剑桥中国文学史》差距甚大。在课程教学实践中,面对通行的袁编教材,出现一些值得思考改进的问题。因受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影响,加上以游编《中国文学史》为代表,逐步建构出“四大奇书”、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牡丹亭、长生殿等明清文学之经典,再发展到袁编《中国文学史》明、清、近代部分,重视小说、戏曲文体,尤其突出上述经典。在学分制课程设置下,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课时明显偏紧[13]。教材对作家作品的轻重决裁,决定我们的教学策略;教师不能轻易的改变教材的选择,因为这样既不利于学生学习,也不符合教学计划的要求。因而在有限的课时中,往往把明、清、近代的文学史教学,变成明、清、近代“经典”小说发展史,而其它文体大都一笔带过。原本复杂多样生机勃勃的文学史,变得生硬僵化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难以提升。当然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必然受到教育制度、学术体制的制约,在引入营塑一批作品的同时,势必要牺牲另一批作品。如果能够在教学中带领学生,适度的走出课本,到其它著述的文学史中去,到课本疆界之外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去,寻找被轻视、忽略的作家作品,这样既有利于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科研意识,有可望逐渐孕育、开拓出新的文学史观。
二、文学史观念构建与课堂教学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萌芽期,因为中国古代对“文学”的定义纷繁不定,且对19世纪末日本、欧美流传过来的文学观念缺乏正确深入地理解,所以早期的文学史有文学观念杂糅的现象。曾毅、谢无量等撰作的《中国文学史》,就被二十世纪30年代的学者认为“其实只是一部国学史”。[14]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的写作,大多摘抄作家的生平资料和引证历代诗文评中对作家的评价;整书详前略后,重诗文轻戏曲。谢无量尽管赞同文学“宗主情感,唯以娱乐为归。虽恒用历史之科学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厥专知,撷其同味,有以挺不朽之盛美焉”[15]。书中忽略文学史结构、文学经典理论体系的功能,有脱离文学文本阅读的撰写倾向;取代的只是作家之后再摘录相关作品,却很少有对作品的分析与评价。又如近世文学第三章论及清代乾嘉文学,第一节为“汉学及考据学之盛”,纯粹属于简要叙述乾嘉汉学代表人物和发展情况,至于其对文学的影响未至一词。萌芽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杂糅,使得著作杂乱无章、观念混淆;但在这种粗糙背后,也让史著涵纳万象,“包容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16]。郑宾于写作的《中国文学流变史》,文学史观念清晰,他说:“文学的源流派别是有变迁和因革的,而这变迁与因革,即是时代的创造”,文学史要“注重各个文学系统的叙述,盖重文学本身系统之流变,而不以朝代的更替划分之也”,“文学史本应以‘文学的范围’为范围,不应窜入其它一切的非文学”。所以郑著基本摒弃了萌芽时期文学史著中掺杂的经学、史学内容,体系严整,内容也有发明之处。但观念明晰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因受进化论文学史观影响过重,认为“文学本是时代的产物”,“当前的便是活的,以往的便是死的”,造成书中“叙诗止于唐,词止于宋,曲止于明而流于清”[17],严重的抹杀了文学自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刘大杰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书写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式作品。刘大杰受法国进化论和社会学派朗松、泰纳、佛里契、勃兰兑斯的文艺理论影响最深,对文学史的观念和著作体裁有着清醒完整的认识。他认为“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学史者的任务,就在叙述他这种进化的过程与状态,在形式上,技巧上,以及那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感,并且特别要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它种种环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