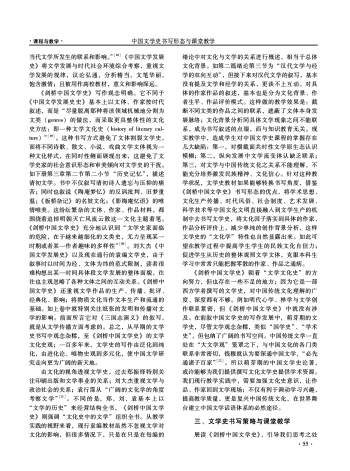《剑桥中国文学史》写作观念明确。它不同于《中国文学发展史史》基本上以文体、作家按时代叙述,而是“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 ”[19]。这种书写方式避免了文体割裂文学史,而将不同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文体视为一种文化样式,在同时性侧面展现出来,这避免了文学史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倾向对文学史的干扰。如下册第三章第二节第二小节“历史记忆”,描述清初文学。书中不仅叙写清初诗人遗忘与压抑的痛苦;同时也叙说《陶庵梦忆》的反讽批判、旧梦重温;《板桥杂记》的名妓文化;《影梅庵忆语》的唯情唯美。这纷纭繁杂的文体、作家、作品材料,都围绕着追掉明朝灭亡风流云散这一文化主题着笔。《剑桥中国文学史》充分地认识到“文学史家面临的危险,在于越来越细化的文类史,无力呈现某一时期或者某一作者趣味的多样性”[2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现在通行的袁编文学史,由于叙事时以时间为经、文体为纬的范式限制,读者很难构想出某一时间具体段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往往也主观忽略了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剑桥中国文学史》还重视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批评、经典化、影响;将物质文化当作文本生产和流通的基础。如上卷中就特别关注纸张的发明和传播对文学的影响。前面所言它对《三国志演义》的叙写,就是从文学传播方面考虑的。总之,从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观念杂糅,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文化史观;一百多年来,文学史的写作由泛化到纯化,由进化论、唯物史观到多元化,使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由文化的视角透视文学史,过去郑振铎特别关注印刷出版和文学事业的关系;刘大杰重视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袁行霈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21]。不同的是,郑、刘、袁基本上以“文学的历史”来经营结构全书,《剑桥中国文学史》则强调“文化史中的文学”组织全书。从教学实践的视野来看,现行袁编教材虽然不忽视文学对文化的影响,但很多情况下,只是在只是在每编的绪论中对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概述,相当于总体文化背景。如第二篇绪论第三节为“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但接下来对汉代文学的叙写,基本没有提及文学和经学的关系,更谈不上互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叙述,基本也是分为文化背景、作者生平、作品评价模式。这样做的教学效果是:截断不同文类的作品之间的联系,遮蔽了文体本身发展脉络;文化背景分析同具体文学现象之间不能联系,成为书写叙述的点缀,而与知识教育无关。现实教学中,造成学生对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掌握存在几大缺陷:第一,对横截面共时性文学原生态认识模糊;第二,纵向发展中文学流变体认缺乏联系;第三,对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不能理解,不能充分培养激发民族精神、文化信心。针对这种教学状况,文学史教材如果能够转换书写角度,借鉴《剑桥中国文学史》书写形态的优点,将学术思想、文化生产传播、时代风俗、社会制度、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等中国文化文明直接融入到文学生产的机制中去书写文学史,将文化因子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上,减少单纯的创作背景分析,这样文学史的“文化学”特性也自然显露出来。如此可望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力;促进学生从历史的整体观照文学文体,克服本科生学习中常常只能把握零散的作家、作品之通病。
《剑桥中国文学史》朝着“文学文化史”的方向努力,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因为它是一部西方学者撰写的文学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广度、深度都有不够。例如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创作联系紧密,但《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就没有涉及。在前叙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发展中,萌芽期的文学史,尽管文学观念杂糅,类似“国学史”、“学术史”,但包纳了广阔的书写空间。中国传统文学一直处在“大文学观”笼罩之下,与中国文化的各门类联系非常密切,钱穆就认为要深通中国文学,“必先通诸子百家”[22]。所以萌芽期的中国文学史论著,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撰写文化文学史提供学术资源。我们现行教学实践中,需要加强文化史意识,让作品、作家回到文学现场;不仅有利于调动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更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建立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然途径。
三、文学史书写策略与课堂教学
展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导我们思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