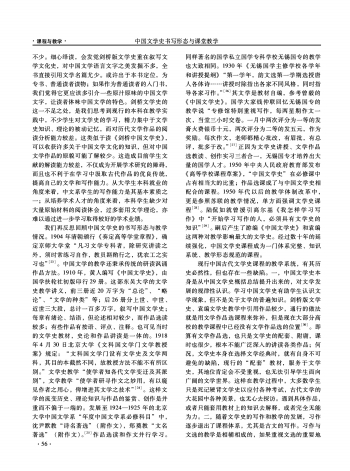我们再反思回顾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教学情况。1904年清朝颁行《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确定京师大学堂“凡习文学专科者,除研究讲读之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农工之实习也”[23]。中国文学的教学还秉承传统的研读讽诵作品方法。1910年,黄人编写《中国文学史》,由国学扶轮社初版印行29册。这部东吴大学的文学史教学讲义,前三册近20万字为“总论”、“略论”、“文学的种类”等;后26册分上世、中世、近世三大段,总计一百多万字,叙写中国文学史;每章有绪论、结语,但论述相对较少,而作品选读较多;有些作品有按语、评点、注释。也可见当时的文学史教材,史论和作品讲读是一体的。1918年4月30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文学史教学“使学者知各代文学变迁及其派别”,文学教学“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24]。这样文学的流变历史、理论知识与作品的鉴赏、创作是并重而不偏于一端的。发展至1924—1925年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年度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中,沈尹默教“诗名著选”(附作文),郑奠教“文名著选”(附作文)。[25]作品选读和作文并行学习。同样著名的国学私立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的教学也大致相同。1930年《无锡国学主修学校各学年和讲授提纲》“第一学年,韵文选第一学期选授唐人各体诗……讲授时除指出各家不同风格,同时指导各家习作。”[26]其文学是教材自编,参考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国学大家钱仲联回忆无锡国专的教学说“专修馆特别重视写作,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当堂三小时交卷。一月中两次评分为一等的发膏火费银币十元,两次评分为二等的发五元,作为奖励。每次作文,老师都精心批改,有眉批,有总评,批多于改。”[27]正因为文学史讲授、文学作品选教读、创作实习三者合一,无锡国专才培养出大量的国学人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草案》,“中国文学史”在必修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品选课成了与中国文学史相配合的课程。1950年代以后的教学体制改革中,更是参照苏联的教学情况,单方面强调文学史课程[28]。陆侃如就曾援引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中“开始学习写作的人,必须具有文学史的知识”[29]。 嗣后产生了游编《中国文学史》和袁编这两种对教学影响最大的文学史。经过数十年的延续强化,中国文学史课程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知识系统、教学形态规范的课程。
现行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系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中国文学史本身是从中国文学史概括总结提升出来的,对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学习中国文学史有助学生认识文学现象,但不是关于文学的普遍知识。剑桥版文学史、袁编文学史教学中引用作品较少,通行的做法就是用文学作品选课程来弥补,但是现在大部分高校的教学课程中已经没有文学作品选的位置[30]。即算有文学作品选,也只是文学史的配套、附庸,课时也很少,根本不能广泛深入的讲读各类作品;何况,文学史本身在选择文学经典时,就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现行的“配套”教材,服务于文学史,其地位肯定会不受重视,也无法引导学生面向广阔的文学世界。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只是死记硬背文学史以应付各种考试,古代文学的大花园中各种美景,也无心去探访。遇到具体作品,或者只能套用教材上的知识去解释,或者完全无能为力。二,随着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的发展,习作逐步退出了课程体系,尤其是古文的写作。习作与文选的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重视文选的重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