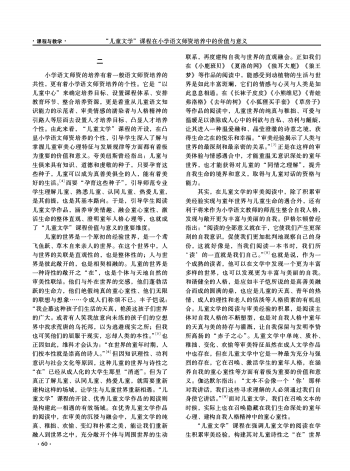小学语文师资的培养有着一般语文师资培养的共性,更有着小学语文师资培养的个性。它是“以儿童中心”来确定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育环节、整合培养资源,更是着重从儿童语文知识能力的示范者、审美情感的濡染者与人格精神的引路人等层面去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凸显人才培养个性。由此来看,“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在凸显小学语文师资培养的个性,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与掌握儿童审美心理特征与发展规律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夸美纽斯曾经指出:儿童与生俱来具有知识、道德和虔敬的种子,只要孕育这些种子,儿童可以成为真善美俱全的人,能有着美好的生活。[4]而要“孕育这些种子”,引导师范专业学生理解儿童、熟悉儿童、认同儿童、热爱儿童,是其前提,也是其基本路向。于是,引导学生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涵养审美情趣、融会童心童性、激活生命的整体直观、澄明童年人格心理等,也就成了“儿童文学”课程价值与意义的重要维度。
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原初的经验世界,是一个鸢飞鱼跃、草木自来亲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是直观性的,也是整体性的;人与世界是彼此敞开的,也是相契相融的。儿童的世界是一种诗性的敞开之“在”,也是个体与天地自然的审美性联结。他们与外在世界的交感,他们蓬勃活跃的生命力,他们绝假纯真的童心童性、他们无限的联想与想象……令成人们称颂不已。丰子恺说:“我企慕这种孩子们生活的天真,艳羡这孩子们世界的广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的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5]也正因如此,维科才会认为:“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崇高的诗人。”[6]但因知识理性、功利意识与社会文化等原因,这种儿童的世界与诗性之“在”已经从成人化的大学生那里“消逝”。但为了真正了解儿童、认同儿童、热爱儿童,就需要重新建构这样的场域,让学生与儿童世界重新相遇。“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则是构建此一相遇的有效场域。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在审美的沉浸与融会中,儿童文学的纯真、稚拙、欢愉、变幻和朴素之美,能让我们重新融入到世界之中,充分敞开个体与周围世界的生动联系,再度建构自我与世界的直观融会。正如我们在《小鹿班贝》《夏洛的网》《独耳大鹿》《狼王梦》等作品的阅读中,能感受到动植物的生活与世界是如此丰富斑斓,它们的情感与心灵与人类是如此息息相通。在《长袜子皮皮》《小熊维尼》《青蛙弗洛格》《去年的树》《小狐狸买手套》《草房子》等作品的阅读中,儿童世界的纯真与稚拙、可爱与温暖足以涤除成人心中的利欲与自私、功利与龌龊,让其进入一种温爱融和、晶莹澄澈的诗意之境,获得生命之在的悦乐和幸福。“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7]正是在这样的审美体验与情感遇合中,才能重温无意识深处的童年世界,也才能获得对儿童的“同情之理解”,提升自我生命的境界和意义,取得与儿童对话的资格与能力。
其实,在儿童文学的审美阅读中,除了积累审美经验实现与童年世界与儿童生命的遇合外,还有利于将来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师范生整合自我人格,发现与敞开更为丰富与美丽的自我。伊格尔顿曾经指出:“阅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产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识,促使我们更加批判地观察自己的身份,这就好像是,当我们阅读一本书时,我们所‘读’的一直就是我们自己。”[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他可以在文学中发现一个更为丰富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发现更为丰富与美丽的自我。和谐健全的人格,是应如丰子恺所说的是真善美融合而成的圆满的鼎,也应是儿童的天真、青年的热情、成人的理性和老人的恬淡等人格质素的有机组合。儿童文学的阅读与审美经验的积累,是阅读主体对自我人格的不断塑型,也是对自我人格中童年的天真与美的持存与灌溉,让自我保留与发明李贽所高扬的“赤子之心”。儿童文学中单纯、质朴、稚拙、变化、欢愉等审美特征虽然在成人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但在儿童文学中它是一种最为充分与强烈的存在,它在召唤、激活学生的童年人格,在涵养自我的童心童性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伽达默尔指出:“文本不会像一个‘你’那样对我讲话,我们这些寻求理解的人必须通过我们自身使它讲话。”[9]面对儿童文学,我们在召唤文本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召唤隐藏在我们生命深处的童年心理、建构自我人格精神中的童心童性。
“儿童文学”课程在强调儿童文学的阅读在学生积累审美经验,构建其对儿童诗性之“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