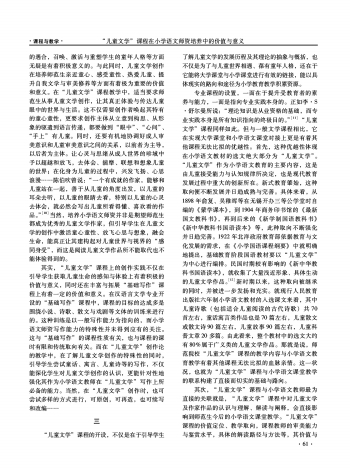其实,“儿童文学”课程上的创作实践不仅在引导学生获取儿童生命的感知与体验上有着积极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在丰富与拓展“基础写作”课程上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基础写作”课程中,课程的目标的达成多是围绕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等文体的训练来进行的。这种训练是以一般写作能力为指向的,而小学语文师资写作能力的特殊性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与“基础写作”的课程性质有关,也与课程的课时有限和传统取向有关。而在“儿童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在了解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的同时,引导学生尝试童话、寓言、儿童诗等的写作,不仅能深化学生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认识,更能针对性地强化其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儿童文学”写作上所必备的能力。当然,在“儿童文学”创作时,也可尝试多样的方式进行,可原创,可再造,也可续写和改编……
三
“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不仅是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的抽象与概括,也不仅是为了与儿童世界相遇、葆有童年人格,还在于它能将大学课堂与小学课堂进行有效的链接,能以具体现实的路向和途径为小学教育教学积累资源。
专业课程的设置,一面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素养与能力,一面是指向专业实践本身的。正如李·S·舒尔曼所说:“理论知识是从业资格的基础,而专业实践本身是所有知识指向的终极目的。”[11]“儿童文学”课程同样如此。但与一般文学课程相比,它在实现大学课堂和小学语文课堂对接上更是有着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首先,这种优越性体现在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绝大部分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是由儿童接受能力与认知规律所决定,也是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重大的创新所在。新式教育肇始,这种取向便不断发展并日趋成熟与完善。具体来看,从1898年俞复、吴稚晖等在无锡开办三等公学堂时自编的《蒙学课本》,到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再到后来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国语读本》等,此种取向不断强化并日趋完善。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依据教育与文化发展的需求,在《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中就明确地提出,基础教育阶段国语教材要以“儿童文学”为中心进行编排。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新中华教科书国语读本》,就收集了大量浅近形象、具体生动的儿童文学作品。[12]新时期以来,这种取向被继承的同时,并被进一步发扬和充实。就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的入选课文来看,其中儿童诗歌(包括适合儿童阅读的古代诗歌)共70首左右,童话寓言类作品也是70篇左右,儿童散文或散文诗90篇左右,儿童故事90篇左右,儿童科普文章20多篇。由此看来,整个教材中的选文大约有80%属于广义类的儿童文学作品。那就是说,师范院校“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有着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血脉亲情。这一状况,也就为“儿童文学”课程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联系构建了直接而切实的基础与路向。
其次,“儿童文学”课程与小学语文教师最为直接的关联就是,“儿童文学”课程中对儿童文学及作家作品的认识与理解、解读与阐释,会直接影响到师范生今后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儿童文学”课程的价值定位、教学取向,课程教师的审美能力与鉴赏水平,具体的解读路径与方法等,其价值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