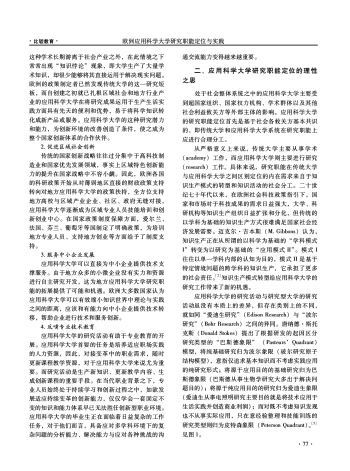2.促进区域社会创新
传统的国家创新战略往往过分集中于高科技制造业和国家优先发展领域,事实上区域特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国家战略中不容小觑。因此,欧洲各国的科研政策开始从对薄弱地区直接的财政政策支持转向对地方应用科学大学的政策扶持,全方位支持地方高校与区域产业企业、社区、政府无缝对接,应用科学大学逐渐成为区域专业人员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中心。在国家政策制度保障方面,爱尔兰、法国、芬兰、葡萄牙等国制定了明确政策,为培训地方专业人员、支持地方创业等方面给予了制度支持。
3.服务中小企业发展
应用科学大学可以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由于地方众多的小微企业没有实力和资源进行自主研究开发,这为地方应用科学大学研究职能的拓展提供了可能和机遇。欧洲大多数国家认为应用科学大学可以有效缩小知识世界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应该和有能力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转移,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和服务创新。
4.反哺专业技术教育
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活动有助于专业教育的开展。应用科学大学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适应职场实践的人力资源,因此,对接变革中的职业需求,随时更新课程教学资源,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来说尤为重要。而研究活动是生产新知识、更新教学内容、生成创新课程的重要手段。在当代职业背景之下,专业人员始终处于持续学习和创新过程之中,如欲发展适应持续变革的创新能力,仅仅学会一套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能力体系早已无法胜任创新型职业环境。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正在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工作任务,对于他们而言,具备应对多学科环境下的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解决能力与应对各种挑战的沟通交流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应用科学大学研究职能定位的理性之思
处于社会整体系统之中的应用科学大学主要受到超国家组织、国家权力机构、学术群体以及其他社会利益攸关方等外部主体的影响。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职能定位首先是基于社会各攸关方基本共识的,即传统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系统在研究职能上应进行合理分工。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传统大学主要从事学术(academy)工作,而应用科学大学则主要进行研究(research)工作。具体来说,研究职能在传统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区别定位的内在需求来自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和知识活动的社会分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欧洲社会科技政策指引下,国家和市场对于科技成果的需求日益强大,大学、科研机构等知识生产组织日益扩张和分化,但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很难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迈克尔·吉本斯(M.Gibbons)认为,知识生产正在从所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模式I”转变为以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模式II”。模式I往往以单一学科内部的认知为目的,模式II是基于特定情境问题的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它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2]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给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活动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活动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存在类别上的不同,就如同“爱迪生研究”(Edison Research)与“波尔研究”(Bohr Research)之间的异同。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提出了根据研发的起因区分研究类型的“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模型,将纯基础研究归为波尔象限(玻尔研究原子结构模型),意指仅追求基本知识而不考虑实践应用的纯研究形式;将源于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归为巴斯德象限(巴斯德从事生物学研究大多出于解决问题目的);将源于纯应用目的的研究归为爱迪生象限(爱迪生从事电照明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将技术应用于生活实践并创造商业利润);而对既不考虑知识发现也不从事实际应用,只在意经验整理和技能训练的研究类型则归为皮特森象限(Peterson Quadrant)。[3]见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