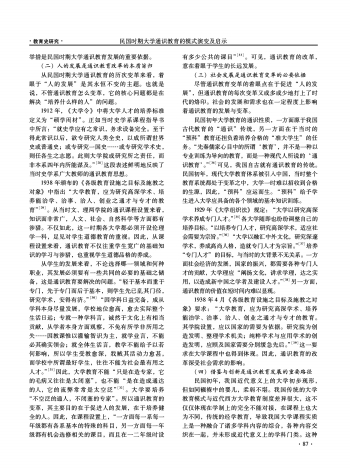(二)人的发展是通识教育改革的本质旨归
从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的历次变革来看,着眼于“人的发展”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也就是说,不管通识教育怎么变革,它的核心问题都是在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1912年,《大学令》中将大学人才的培养标准定义为“硕学闳材”。正如当时史学系课程指导书中所言:“就史学应有之常识,务求设备完全。至于得此常识以后,欲专研究人类全史,以成所谓世界史或普通史;或专研究一国史……或专研究学术史,则任各生之志愿。此则大学院或研究所之责任,而非本系四年内所能谋及。”[28]这段表述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史学系广大教师的通识教育思想。
1938年颁布的《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之对象》中指出“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的教育”[29]。从当时文、理两学院的通识课程设置来看,知识面非常广,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涉猎。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各大学都必须开设伦理学一科,足见对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视。因此,从课程设置来看,通识教育不仅注重学生宽广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涉猎,也重视学生道德品格的养成。
从学生的发展来看,不论选择哪一领域和何种职业,其发展必须要有一些共同的必要的基础之储备,这是通识教育要解决的问题。“轻于基本而重于专门,先于专门而后于基本,则学生先已乱其门径,研究学术,安得有济。”[30]“因学科日益完备,咸从学科本身尽量发展,学校地位愈高,愈去实际整个生活日远;专就一种学科言,诚然于文化上有相当贡献,从学者本身方面观察,不免有所学非所用之失……因教课惟以灌输智识为主,就学业言,不能必其确实领会;就全体生活言,教学不能给予以若何影响,所以学生受教愈深,戕贼其活动力愈甚,而学校中所谓最好学生,往往不能为社会最有用之人才。”[31]因此,大学教育不能“只是在造专家,它的毛病又往往是太闭塞”,也不能“是在造成通达的人,它的流弊常常是太空泛”[32]。大学要培养“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所以通识教育的变革,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健全的人。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每一系每一年级都有各系基本的特殊的科目,另一方面每一年级都有机会选修相关的课目,而且在一二年级时设有多少公共的课目”[33]。可见,通识教育的改革,意在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三)社会发展是通识教育变革的必要依据
尽管通识教育变革的着眼点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但通识教育的每次变革又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通识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民国初年大学教育的通识性质,一方面源于我国古代教育的“通识”传统,另一方面在于当时的“预科”教育还担负着培养合格的“准大学生”的任务。“先秦儒家心目中的所谓‘教育’,并不是一种以专业训练为导向的教育,而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通识教育’。”[34]可见,我国自古就有通识教育的传统。民国初年,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被引入中国,当时整个教育系统都处于变革之中,大学一时难以招收到合格的生源,因此,“预科”应运而生。“预科”给予学生进入大学应具备的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训练。
1929年《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35]各大学随即也纷纷调整自己的培养目标。“以培养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术,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36]“大学以融汇中外文化,研究深邃学术,养成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37]培养“专门人才”的目标,与当时的大背景不无关系。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振兴,都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贡献,大学理应“阐扬文化,讲求学理,达之实用,以造成新中国之学者及建设人才。”[38]另一方面,通识教育的价值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
1938年4月《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之对象》要求:“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的教育。其学院设置,应以国家的需要为依据。研究院为创造发明、整理学术机关;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的创造发明,应顾及国家需要分别缓急先后。”[39]这一要求在大学课程中也得到体现。因此,通识教育的改革深受社会需求的影响。
(四)借鉴与创新是通识教育发展的重要路径
民国初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初步现形,但如同襁褓中的婴儿,柔弱不堪。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模式与近代西方大学教育制度差异很大,这不仅仅体现在学制上的完全不能对接,在课程上也大为不同,传统的经学教育,导致我国大学课程实质上是一种融合了诸多学科内容的综合,各种内容交织在一起,并未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