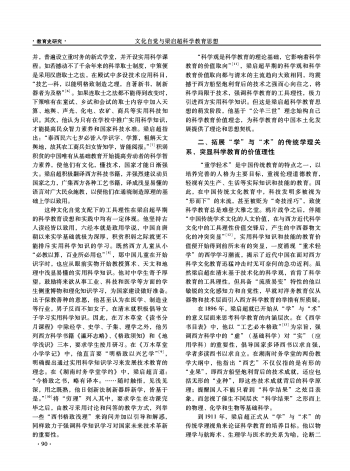这种文化自觉支配下的工具理性在梁启超早期的科学教育设想和实践中均有一定体现。他坚持古人读经皆以致用,六经本就是致用学说,中国自唐朝以来实学基础就极为深厚,积贫积弱之际就更不能排斥实用科学知识的学习。既然西方儿童从小“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8],那中国儿童在开始识字时,也应从眼前实物开始教授算术、天文和地理中浅显易懂的实用科学知识。他对中学生寄予厚望,鼓励将来欲从事工业、科技和医学等方面的学生侧重博物和理化知识学习,为国家建设做好准备。出于保教善种的意愿,他甚至认为在医学、制造业等行业,男子反而不如女子,在清末就积极倡导女子学习实用科学知识。因此,在万木草堂《读书分月课程》中除经学、史学、子集、理学之外,他另列西方科学书籍《瀛环志略》、《格致须知》和《地学浅识》三本,要求学生按月研习。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他直言要“明格致以兴艺学”[9],明确提出通过实用科学知识学习来发展技术教育的理念。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言道:“今格致之书,略有译本。……随时触悟,见浅见深,用之既熟,他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皆基于是。”[10]将“穷理”列入其中,要求学生在功课完毕之后,由教习采用讨论和问答的教学方式,列举一些“西书格致浅理”来询问并加以引导和解惑,同样致力于强调科学知识学习对国家未来技术革新的重要性。
“科学观是科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它影响着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11],梁启超早期的科学观和科学教育价值取向都与清末的主流趋向大致相同,均震撼于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技术之强而心向往之,将科学局限于技术,强调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极力引进西方实用科学知识。但这是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的萌发阶段,他基于“公羊三世”理念始构自己的科学教育价值理念,为科学教育的中国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契机。
二、拓展“学”与“术”的传统学理关系,突显科学教育的价值理性
“重学轻术”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之一,以培养完善的人格为主要目标,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轻视有关生产、生活等实际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科技发明多被视为“形而下”的末流,甚至被贬为“奇技淫巧”,致使科学教育总是难登大雅之堂。鸦片战争之后,伴随“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人文价值,在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价值交锋后,产生的中西器物文化的冲突突显”[12],实用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价值便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突显,一度涌现“重术轻学”的西学学习潮流,揭示了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科学文化教育迅猛冲击时无可奈何的急功近利。虽然梁启超在清末基于技术化的科学观,首肯了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但具备“流质易变”特性的他以敏锐的文化感知力和自觉性,早就对洋务教育仅从器物和技术层面引入西方科学教育的举措有所质疑。
在1896年,梁启超就已开始从“学”与“术”的意义层面来思考科学教育的内涵层次。在《西学书目表》中,他以“工艺必本格致”[13]为宗旨,强调西方科学中的“虚”(基础科学)对“实”(应用学科)的重要性,倡导国家多译西书以求自强,学者多读西书以求自立。在湖南时务学堂的两份教学大纲中,他指出“西艺”不仅仅指的是有形的“业果”,即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技术成就,还应包括无形的“业种”,即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科学原理;提醒国人不能只看到“科学结果”之炫目表象,而忽视了催生不同层次“科学结果”之形而上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
到1911年,梁启超正式从“学”与“术”的传统学理视角来论证科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他以物理学与航海术、生理学与医术的关系为喻,论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