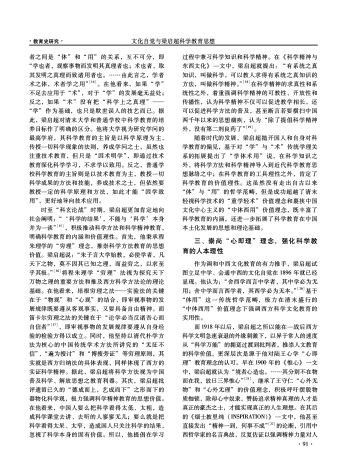时至“科玄论战”时期,梁启超更加肯定地向社会阐明:“‘科学的结果’,不能与‘科学’本身并为一谈”[15],积极推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教育,明确科学教育的内涵和价值理性。首先,他秉承程朱理学的“穷理”理念,推崇科学方法教育的思想价值。梁启超说:“朱子言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16]将程朱理学“穷理”法视为探究天下万物之理的重要方法和推及西方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培根穷理之法——实验法的关键在于“物观”和“心观”的结合,即审视事物的发展规律既要遵从客观事实,又要具备自由精神。而笛卡尔穷理之法的关键在于“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17],即审视事物的发展规律要遵从自身经验的检验方得以成立。同时,他坚持以清代朴学方法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所讲究的“无征不信”、“遍为搜讨”和“博搜旁证”等穷理原则,其实就是西方归纳法的具体表现,同样体现了西方的实证科学精神。据此,梁启超将科学方法视为中国普及科学、解放思想之教育利器。其次,梁启超批评遗留已久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形而下的器物化科学观,极力强调科学精神教育的思想价值。在他看来,中国人要么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造成科学课堂去讲、去听的人寥寥无几;要么就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造成国人只关注科学的结果,忽视了科学本身的固有价值。所以,他提倡在学习过程中兼习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梁启超就提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8]在科学精神的求真性和系统性之外,着重强调科学精神的可教性、开放性和传播性,认为科学精神不仅可以促进教学相长,还可以促进科学方法的普及,甚至断言若要横扫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思想痼疾,认为“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19]。
随着时代的发展,梁启超抛开国人和自身对科学教育的偏见,基于对“学”与“术”传统学理关系的拓展提出了“学体术用”说,在科学知识之外,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导入到近代科学教育思想脉络之中;在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之外,肯定了科学教育的价值理性。这虽然没有走出自古以来“体”与“用”的哲学范畴,但是成功超越了清末轻视科学技术的“重学轻术”价值理念和裹挟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价值理念,既丰富了科学教育的内涵,还进一步拓展了科学教育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崇尚“心即理”理念,强化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
作为调和中西文化教育的有力推手,梁启超试图立足中学、会通中西的文化自觉在1896年就已经显现。他认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20]基于“体用”这一传统哲学范畴,极力在清末盛行的“中体西用”价值理念下强调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实用性。
而1918年以后,梁启超之所以能在一战后西方科学文明急速衰退的外缘刺激下,以异于常人的速度从“科学万能”的拥趸过渡到批判者,推崇人文教育的科学价值,更深层次是源于他对陆王心学“心即理”教育理念的认可。早在1900年的《惟心》一文中,梁启超就认为“境者心造也。……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21],继承了王守仁“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的价值理念,积极呼吁摆脱物质枷锁,除却心中奴隶,赞扬追求精神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豪杰之士,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理想。在其后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一文中,他甚至直接发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22]的论断,引用中西哲学家的名言典故,反复佐证以强调精神力量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