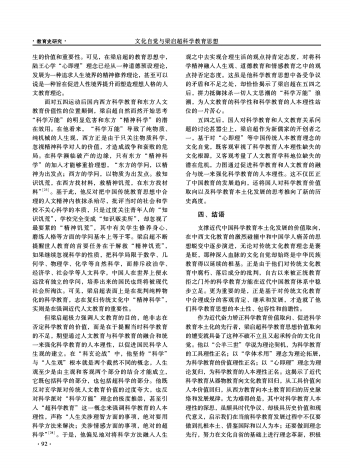面对五四运动后国内西方科学教育和东方人文教育价值性的位置颠倒,梁启超自然而然开始思考“科学万能”的明显危害和东方“精神科学”的潜在效用。在他看来,“科学万能”导致了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西方正是由于只关注物质科学,忽视精神科学对人的价值,才造成战争和衰败的危局。在科学濒临破产的边缘,只有东方“精神科学”的加入才能够重拾理想,“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23]。基于此,他反对把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合理的人文精神内核抹杀殆尽,批评当时的社会和学校不关心科学的本质,只是过度关注青年人的“知识饥荒”,学校完全变成“知识贩卖所”,却忽视了最要紧的“精神饥荒”,其中有关学生修养身心、磨练人格等方面的学问基本上等于零。梁启超不断提醒世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解救“精神饥荒”,如果继续忽视科学的性质,把科学局限于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而排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独立的学问,培养出来的国民也终将被现代社会所淘汰。可见,梁启超表面上是在批判纯粹物化的科学教育,志在复归传统文化中“精神科学”,实则是在强调近代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但梁启超极力强调人文教育的目的,绝非志在否定科学教育的价值,而是在于提醒当时科学教育的不足,期望通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和统一来强化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以促进国民科学人生观的建立。在“科玄论战”中,他坚持“科学”与“人生观”根本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人生观至少是由主观和客观两个部分的结合才能成立,它既包括科学的部分,也包括超科学的部分。他既反对玄学派对传统人文教育价值的过度夸大,也反对科学派对“科学万能”理念的极度推崇,甚至引入“超科学教育”这一概念来强调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声称“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24]。于是,他偏见地对将科学方法融入人生观之中去实现合理生活的观点持肯定态度,对将科学精神融入人生观、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之中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这虽是他科学教育思想中备受争议的矛盾和不足之处,却恰恰揭示了梁启超在五四之后,拼力抵御抹杀一切人文思潮的“科学万能”浪潮,为人文教育的科学性和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站位的一片苦心。
五四之后,国人对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关系问题的讨论甚嚣尘上,梁启超作为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基于对“心即理”等中国传统人本教育理念的文化自觉,既客观审视了科学教育人本理性缺失的文化根源,又客观考量了人文教育学科地位缺失的潜在危机,力图通过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与统一来强化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这不仅匡正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向,还将国人对科学教育价值取向以及科学教育本土化发展的思考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四、结语
支撑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本土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在中西文化教育的激烈碰撞中和中国学人痛苦的思想蜕变中逐步演进,无论对传统文化教育理念是褒是贬,那种深入血脉的文化自觉却始终是中华民族教育得以延续的根基。正是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教育中腐朽、落后成分的批判,自古以来被正统教育拒之门外的科学教育方能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稳步立足。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教育中合理成分的客观肯定、继承和发展,才造就了他们科学教育思想的本土性、包容性和前瞻性。
作为近代奋力矫正科学教育价值取向、促进科学教育本土化的先行者,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嬗变就具备了这种不破不立且又起承转合的文化自觉。他以“公羊三世”学说为理论契机,为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正名;以“学体术用”理念为理论拓展,为科学教育的价值理性正名;以“心即理”理念为理论复归,为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正名。这揭示了近代科学教育从器物教育向文化教育回归,从工具价值向人本价值回归,从西方教育向本土教育回归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尤为难得的是,其中对科学教育人本理性的深思,虽颇具时代争议、却极具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启示我们在当前科学教育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做到扎根本土、借鉴国际和以人为本;还要做到理念先行,努力在文化自省的基础上进行理念革新,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