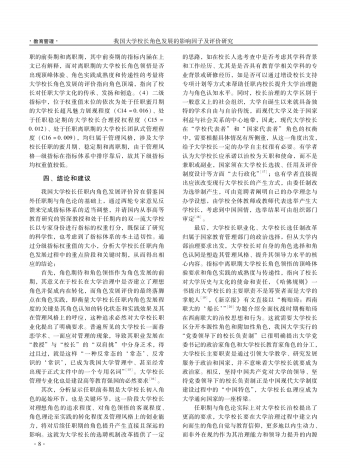职的前奏期和离职期,其中前奏期的指标内涵在上文已有解释,而对离职期的大学校长角色领悟是否出现顶峰体验、角色实践成熟度和传递性的考量将大学校长角色发展的评价指向角色顶端,指向了校长对任职大学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创造。(4)二级指标中,位于权重值末位的依次为处于任职蜜月期的大学校长超凡魅力展现程度(C14=0.016)、处于任职稳定期的大学校长合理授权程度(C15=0.012)、处于任职离职期的大学校长团队式管理程度(C16=0.009),均归属于管理风格,涉及大学校长任职的蜜月期、稳定期和离职期,由于管理风格一级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排序靠后,故其下级指标均权重值较低。
四、结论和建议
我国大学校长任职内角色发展评价旨在借鉴国外任职期与角色论的基础上,通过两轮专家意见反馈来完成指标体系的适当调整,并请国内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资深教授和处于任期内的双一流大学校长以专家身份进行指标的权重打分,既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也考虑到了指标体系的本土适切性。通过分级指标权重值的大小,分析大学校长任职内角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阶段和关键时期,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首先,角色期待和角色领悟作为角色发展的前期,其意义在于校长在大学治理中是否建立了理想角色并促成内在转化,而角色发展评价的最终落脚点在角色实践,即衡量大学校长任职内角色发展程度的关键是其角色认知的转化状态和实践效果及其在管理风格上的呼应,这种追求必然对大学校长职业化提出了明确要求。普遍所见的大学校长一面眷恋学术、一面应对管理的现象,导致其职业发展在“教授”与“校长”的“双肩挑”中分身乏术,得过且过,就是这样“一种反常态的‘常态’、反常识的‘常识’,已成为我国大学管理中、甚至经常出现于正式文件中的一个专用名词”[15]。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16]。
其次,分析显示任职前奏期是大学校长初入角色的起始环节,也是关键环节,这一阶段大学校长对理想角色的追求程度、对角色领悟的客观程度、角色理论至实践的转化程度及管理风格上的创业能力,将对后续任职期的角色提升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这就为大学校长的选聘机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如在校长人选考查中是否考虑其学科背景和工作经历、尤其是是否具有教育学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或研修经历,如是否可以通过增设校长支持专项计划等方式来帮助任职内校长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与角色认知水平。同时,校长治理的大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大学自诞生以来就具备独特的学术自由与自治传统,而现代大学又处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关系的中心地带,因此,现代大学校长在“学校代表者”和“国家代表者”角色的权衡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从这一角度出发,给予大学校长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很有必要。有学者认为大学校长应承诺以治校为天职和使命,而不是兼职或副业,国家须在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及评价制度设计等方面“去行政化”[17];也有学者直接提出应该改变现行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由委任制改为选举制产生,可由竞聘者阐明自己的办学理念与办学设想,由学校全体教师或教师代表选举产生大学校长,考虑到中国国情,选举结果可由组织部门审定[18]。
最后,大学校长职业化、大学校长选任制改革归属于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的政治选择,但从大学内部治理要求出发,大学校长对自身的角色选择和角色认同是塑造其管理风格、提升其领导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指标中离职期大学校长角色领悟的顶峰体验要求和角色实践的成熟度与传递性,指向了校长对大学历史与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哈佛规则》一书提出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不是筹资者而是大学的掌舵人[19],《新京报》有文直接以“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20]为题介绍全面抗战时期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的治校思想和行为。这就需要大学校长区分开本源性角色和附加性角色,我国大学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已很明确提出大学党委书记的政治家角色和大学校长教育家角色的分工,大学校长主要职责是通过引领大学教学、研究发展服务于政治和国家,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就要成为政治家。相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大学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正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大学校长也理应成为大学通向国家的一座桥梁。
任职期与角色论实际上对大学校长治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校长要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建立内向而生的角色自觉与教育信仰,更多地以内生动力、而非外在规约作为其治理能力和领导力提升的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