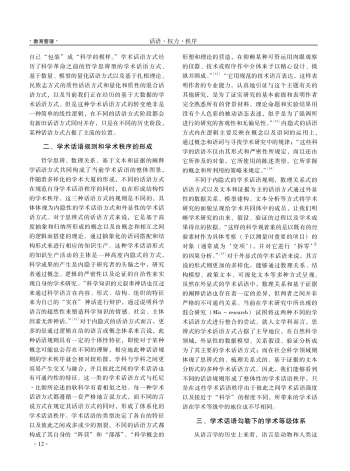自己“包装”成“科学的模样。”学术话语方式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前的哲学思辨型的学术话语方式、基于数量、模型的量化话语方式以及基于扎根理论、民族志方式的质性话语方式和量化和质性的混合话语方式,以及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基于大数据的学术话语方式。但是这种学术话语方式的转变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逻辑,在不同的话语方式阶段都会有新旧话语方式同时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种话语方式占据了主流的位置。
二、学术话语规则和学术秩序的形成
哲学思辨、数理关系、基于文本和证据的阐释学话语方式共同构成了当前学术话语的整体图景,伴随着多样化的学术大厦的形成,不同的话语方式在规范自身学术话语秩序的同时,也在形成结构性的学术秩序。这三种话语方式的规则是不同的,具体体现为内隐性的学术话语方式和外显性的学术话语方式。对于思辨式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基于高度抽象和归纳所形成的概念以及由概念和相互之间的逻辑而搭建的理论。通过抽象化的语词搭配和结构形式来进行相应的知识生产。这种学术话语形式的知识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一种高度内隐式的方式,科学成果的产生是内隐于研究者的头脑之中,研究者通过概念、逻辑的严密性以及论证的自洽性来实现自身的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的元叙事神话也反过来通过科学语言在内容、形式、结构、组织的特征来为自己的“实在”神话进行辩护,通过说明科学语言的超然性来塑造科学知识的情感、社会、主体因素无涉神话。”[11]对于内隐式的话语方式而言,更多的是通过逻辑自洽的语言或概念体系来言说,此种话语规则具有一定的个体性特征,即使对于某种概念可能也会存在不同的理解,相应地此种话语规则的学术秩序就会相对较松散,学科与学科之间更容易产生交叉与融合,并且彼此之间的学术话语也有可通约性的特征。这一类的学术话语方式与托尼·比彻所论述的软科学有着相似之处。每一种学术话语方式都遵循一套严格地言说方式,而不同的言说方式在规定其话语方式的同时,形成了体系化的学术话语秩序。学术话语的类型决定了各自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或多或少的割裂。不同的话语方式都构成了其自身的“阵营”和“部落”。“科学概念的形塑和理论的营造,在仰赖某种可资运用肉眼观察的仪器、技术或程序作中介体来予以精心设计、操纵并圆成。”[12]“它用规范的技术语言表达,这样表明作者的专业能力。认真地引证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其他研究,是为了证实研究的基本前提和表明作者完全熟悉所有的背景材料。理论命题和实验结果用没有个人色彩的被动语态表述,似乎是为了强调所进行的研究的客观性和无偏见性。”[13]内隐式的话语方式内在逻辑主要反映在概念以及语词的运用上,通过概念和语词与寻找学术研究中的规律;“这些科学的话语不仅由其形式和严密性所规定,而且还由它所涉及的对象,它所使用的陈述类型,它所掌握的概念和所利用的策略来规定。”[14]
不同于内隐式的学术话语规则,数理关系式的话语方式以及文本和证据为主的话语方式通过外显性的数据关系、模型建构、文本分析等方式将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给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让我们明晰学术研究的由来、假设、验证的过程以及学术成果得出的依据。“这样的科学观着重的是以既有的经验素材作为具体考察(予以测量时重要的项目)的对象(通常成为‘变项’),并对它进行‘拆零’②的因果分析。”[15]对于外显式的学术话语来说,其言说的形式则更加的多样化,能够通过数理关系、结构模型、政策文本、可视化文本等多种方式呈现。虽然在外显式的学术话语中,数理关系和基于证据的阐释话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并非严格的不可通约关系。当前在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混合研究(Mix-research)试图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进行整合的尝试。就人文学科而言,思辨式的学术话语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外显性的数据模型、关系假设、验证分析成为了其主要的学术话语方式;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体现了思辨式的、梳理关系式的、基于证据的文本分析式的多种学术话语方式。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话语规则形成了整体性的学术话语秩序,只是在这些学术话语秩序由于彼此之间学术话语强度以及接近于“科学”的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等级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三、学术话语勾勒下的学术等级体系
从语言学的历史上来看,语言是动物和人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