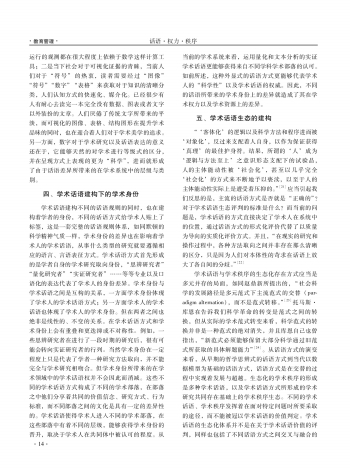运行的观测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这样计算工具;二是当下社会对于可视化证据的青睐,当前人们对于“符号”的热衷,读者需要经过“图像”“符号”“数字”“表格”来获取对于知识的清晰分类,人们认知方式的快速化、媒介化。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去读完一本完全没有数据、图表或者文字以外装扮的文章。人们厌倦了传统文字所带来的平淡,而可视化的图像、表格、结构图形在提升学术品味的同时,也在迎合着人们对于学术美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数字对于学术研究以及话语表达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天然的对学术进行等级式的区分,并在呈现方式上表现的更为“科学”,进而就形成了由于话语差异所带来的在学术系统中的层级与类别。
四、学术话语建构下的学术身份
学术话语建构不同的话语规则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学者的身份,不同的话语方式给学术人贴上了标签,这是一套完整的话语规则体系,如同默顿的科学精神气质一样,学术身份的差异也在影响着学术人的学术话语,从事什么类型的研究就要遵循相应的语言、言语表征方式。学术话语方式首先形成的是学者自身的学术研究取向身份,“思辨研究者”“量化研究者”“实证研究者”……等等专业以及口语化的表达代表了学术人的身份差异。学术身份与学术话语之间是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学术身份体现了学术人的学术话语方式;另一方面学术人的学术话语也体现了学术人的学术身份。但在两者之间也绝非是线性的、不变的关系。在学术话语方式和学术身份上会有重叠和更迭抑或不对称性。例如,一些思辨研究者在进行了一段时期的研究后,很有可能会转向实证研究者的行列。当然学术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代表了学者一种研究方法取向,并不能完全与学术研究相吻合。但学术身份所带来的在学术领域中的学术话语权并不会因此而消减。这些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学术部落,在部落之中他们分享着共同的价值信念、研究方式、行为标准,而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学术话语使得学术人进入不同的学术部落,在这些部落中有着不同的层级,能够获得学术身份的晋升,取决于学术人在共同体中被认可的程度。从当前的学术系统来看,运用量化和文本分析的实证学术话语更能够获得来自不同学科学术部落的认可。如前所述,这种外显式的话语方式更能够代表学术人的“科学性”以及学术话语的权威。因此,不同的话语所带来的学术身份上的差异就造成了其在学术权力以及学术资源上的差异。
五、学术话语生态的建构
“‘客体化’的逻辑以及科学方法和程序进而被‘对象化’,反过来支配着人自身,以作为保证获得‘真理’的最佳护身符。结果,所谓的‘人’成为‘逻辑与方法至上’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试验品,人的主体能动性被‘社会化’,甚至以几乎完全‘社会化’的方式来不断地予以亵渎,以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实际上是遭受着压抑的。”[21]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是,主流的话语方式是否就是“正确的”?对于学术话语生态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而当前的问题是,学术话语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学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通过话语方式的形式化评价代替了以质量为导向的实质化评价方式。并且,“在现实的研究和操作过程中,各种方法取向之间并非存在那么清晰的区分,只是因为人们对本体性的苛求在话语上放大了各自间的分歧。”[22]
学术话语与学术秩序的生态化存在方式应当是多元并存的局面,如同赵鼎新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而不是范式转移。”[23]托马斯·库恩在告诉我们科学革命的转变是范式之间的转换,但从实际的学术范式转变来看,科学范式的转换并非是一种范式的绝对消失,并且库恩自己也曾指出,“新范式必须能够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24]。从话语方式的演变来看,从早期的哲学思辨式的话语方式到当代以数据模型为基础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是在交替的过程中实现着发展与超越。生态化的学术秩序的形成是多种学术话语,以及学术话语方式所形成的学术研究共同存在基础上的学术秩序生态。不同的学术话语、学术秩序发挥着在面对特定问题时所要采取的途径,而不能被冠以学术话语的价值判定。学术话语的生态化体系并不是在关于学术话语价值的评判,同样也包括了不同话语方式之间交叉与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