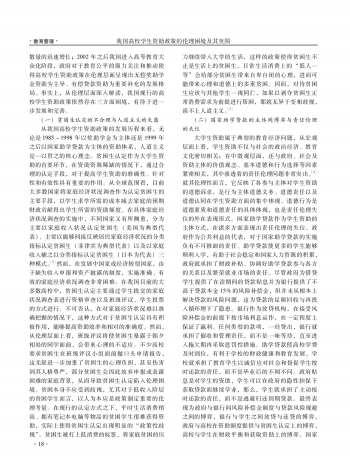数量的迅速增长;2002年之后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政府对于教育公平的强力关注和推动使得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在伦理层面呈现出无偿奖助学金资助为主导、有偿贷款资助为重要补充的发展格局。事实上,从伦理层面深入解读,我国现行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依然存在三方面困境,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贫困生认定的不合理与人道主义的失落
从我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1985-1998年以奖助学金为主体还是1999年之后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资助体系,人道主义是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贫困生认定作为大学生资助的首要环节,在资助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认定手段,对于提高学生资助的准确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作为认定贫困生的主要手段,以学生求学所需的成本减去家庭的预期财政贡献得出学生所需的资助额度。在具体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实施中,不同国家又有所侧重,分为主要以家庭收入状况认定贫困生(美国为典型代表)、主要以能够间接反映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分类指标认定贫困生(菲律宾为典型代表)以及以家庭收入辅之以分类指标认定贫困生(日本为代表)三种模式。[2]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缺失收入申报和资产披露的制度,实施准确、有效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非常困难。在我国目前的大多数高校中,贫困生认定主要通过学生提交的家庭状况调查表进行资格审查以及班级评议、学生投票的方式进行。不可否认,在对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准确把握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对于贫困生认定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提高资助效率和相对的准确度。然而,从伦理层面上看,班级评议将使贫困生暴露于朝夕相处的同学面前,会带来心理的不适应。不少高校要求贫困生在班级评议小组面前做口头申请报告,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贫困生的心理负担,甚至伤害到其人格尊严,部分贫困生会因此放弃申报或表露困难的家庭背景,从而导致贫困生认定陷入伦理困境。贫困本身不应受到歧视,尤其对于低收入阶层的贫困学生而言,以人为本应是政策制定重要的伦理考量。在现行的认定方式之下,平时生活消费稍高、拥有笔记本电脑等物品的贫困学生很难获得资助,实际上使得贫困生认定出现明显的“政策性歧视”。贫困生被打上低消费的标签,将家庭贫困的压力继续带入大学的生活,这样的政策使得贫困生不止是生活上的贫困生,日常生活消费上的“低人一等”会给部分贫困生带来自卑自闭的心理,进而可能带来心理和道德上的多重贫困。因而,对待贫困生应该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如果以剥夺贫困生正常消费需求为前提进行帮困,那就无异于变相歧视,谈不上人道主义。[3]
·教育管理·我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伦理困境及其突围
(二)国家助学贷款的主体间博弈与责任伦理的失位
大学生资助属于典型的教育经济问题,从宏观层面上看,学生资助不仅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密切相关;在中微观层面,还与政府、社会及资助主体的价值观念、基本道德和行为选择等因素紧密相关,其中渗透着的责任伦理问题非常突出。[4]就其伦理性而言,它反映了各参与主体对学生资助的道德诉求,是行为主体道德义务、道德责任以及道德认同在学生资助方面的集中体现。道德行为是道德素质和道德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责任伦理失位的外在表现形式。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学生资助的主体方式,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责任伦理的失位。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助学贷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顺利入学,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人力资源的积累,政府就承担了财政补贴、协调好助学贷款参与各方的关系以及繁荣就业市场的责任。尽管政府为借贷学生提供了在读期间的贷款贴息并为银行提供了不高于贷款本金15%的风险补偿金,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贷款的风险问题,这为贷款的足额回收与再投入循环埋下了隐患。银行作为放贷机构,在接受风险补偿金的前提下按市场利息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赢利。任何类型的款项,一经贷出,银行就承担了催收和管理责任,而不是一味等待,直至进入拖欠期再采取惩罚性措施。助学贷款使高校学费及时到位,有利于学校的财政健康和教育发展,学校就承担了教育学生以诚信应对社会和督促学生按时还款的责任,而不是毕业后的不闻不问。政府贴息是对学生的资助,学生可以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获取贷款而继续学业,那么,学生就承担了主动按时还款的责任,而不是逃避归还到期贷款。最终表现为政府与银行间风险补偿金额度与贷款风险规避之间的博弈,银行与学生之间放贷与还贷的博弈,政府与高校在资助额度提供与贫困生认定上的博弈,高校与学生在财政平衡和获取资助上的博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