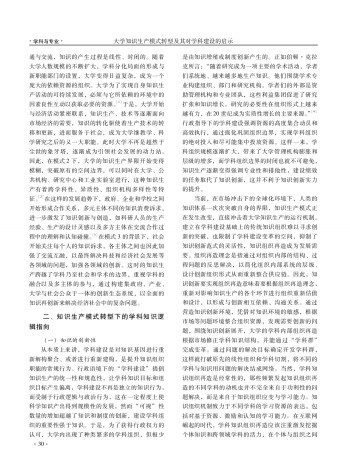通与交流,知识的产生过程是线性、封闭的。随着大学人数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科分化局面的形成与新职能部门的设置,大学变得日益复杂,成为一个庞大的依赖资源的组织。大学为了实现自身知识生产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良性互动以获取必要的资源。[1]于是,大学开始与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知识生产、技术等逐渐面向市场经济的需要,知识的转化驱使着生产技术的转移和更新,进而服务于社会,成为大学继教学、科学研究之后的又一大职能。此时大学不再是超然于尘世的象牙塔,逐渐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因此,在模式2下,大学的知识生产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突破原有的空间边界,可以同时在大学、公共机构、研究中心和工业实验室进行,这种知识生产有着跨学科性、异质性、组织机构多样性等特征。[2]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开始形成合作关系,多元主体不同的知识消费诉求,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创新与创造,如科研人员的生产经验、生产的设计灵感以及多方主体在交流合作过程中的理解和认知碰撞。[3]在模式3的背景下,社会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知识诉求,各主体之间也因此加强了交流互融,以最终解决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领域的问题,加强各领域的创新。这时的知识生产跨越了学科乃至社会和学术的边界,重视学科的融合以及多主体的参与,通过构建集政府、产业、大学与社会公众于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全面的知识再创新来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学科与专业·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其对学科建设的启示
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的学科知识逻辑指向
(一)知识的创新性
从本质上来讲,学科建设是对知识基因进行重新解构聚合、或者进行重新建构,是提升知识组织职能的常规行为。行政语境下的“学科建设”提倡知识生产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让学科知识目标和组织目标产生偏离,学科建设不再是独立的知识行为,而受制于行政逻辑与政治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知识产出得到规模性的发展,然而“可视”性数量的增加超越了知识和制度的创新,建设学科组织的重要性强于知识。于是,为了获得行政权力的认可,大学内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学科组织,但极少是由知识增殖或制度创新产生的。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随着研究成为一项主要的学术活动,学者们系统地、越来越多地生产知识。他们围绕学术专业构建组织、部门和研究机构。学者们的外部是资助管理机构和专业团队,这些利益集团促进了研究扩张和知识增长。研究的必要性在组织形式上越来越有力,在20世纪成为实质性增长的主要来源。”[4]行政指导下的学科建设强调资源的高度集合动员和高效执行,通过强化巩固组织边界,实现学科组织的绝对投入和尽可能集中投放资源。这样一来,学科组织规模逐渐扩大,带来了大学管理机构膨胀和层级的增多,而学科组织边界的封闭也就不可避免,知识生产逐渐变得强调专业性和排他性,建设绩效的任务取代了知识创新,这并不利于知识创新实力的提升。
当前,在市场冲击下的全球化环境下,人类的知识体系一次次突破自身的界限,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直接冲击着大学知识生产的运行机制。建立在学科建设基础上的传统知识组织难以寻求创新的突破,也限制了学科建设变革的空间,抑制了知识创新范式的灵活性,知识组织再造成为发展需要。组织再造理念是指通过对组织内部的结构、过程问题的反思解决,以简化组织内部系统的层级、设计创新组织形式从而重新整合供应链。因此,知识创新要实现组织再造意味着要根据组织再造理念,重新对影响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重新估值和设计,以形成与创新相互依赖、沟通关系。通过营造知识创新环境,凭借对知识环境的敏感,根据市场等问题环境整合组织资源,发现需要创新的问题,围绕知识创新展开,大学的学科内部组织再造根据市场修正学科知识结构,并能通过“学科群”完成变革。通过问题的解决目标确定开发学科群,这样就打破原先的线性组织和学科切割,将不同的学科与知识用问题的解决结成网络。当然,学科知识组织再造是经常性的,那些频繁发起知识组织再造的不同学科的动机也并不完全来自于功利性的问题解决,而是来自于知识组织应变与学习能力。知识组织机制致力于不同学科的学习资源的表达,包括对基于资源、激励和认知的学习能力。在互联网崛起的时代,学科知识组织再造应该注重激发挖掘个体知识和跨领域学科的活力,在个体与组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