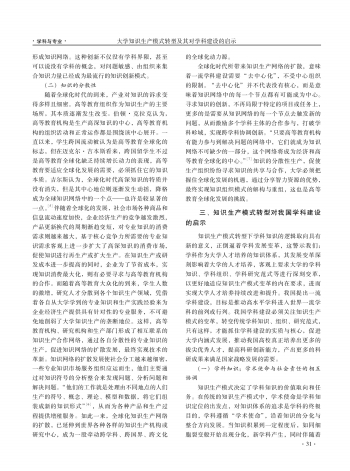形成知识网络。这种创新不仅没有学科界限,甚至可以说没有学科的概念,对问题敏感、由组织来集合知识力量已经成为最流行的知识创新模式。
(二)知识的分散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产业对知识的诉求变得多样且细密。高等教育组织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其本质逐渐发生改变。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是生产高深知识的中心,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活动和正常运作都是围绕该中心展开。一直以来,学生跨国流动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标志,但在迈克尔·吉本斯看来,跨国留学生不过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缺乏持续增长动力的表现,高等教育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必须抓住它的知识本质。吉尔斯认为,全球化时代高深知识的特质并没有消失,但是其中心地位则逐渐发生动摇,降格成为全球知识网络中的一个点——也许是较显著的一点。[5]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市场各种商品和信息流动速度加快,企业经济生产的竞争越发激烈,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渐趋变短,对专业知识的消费需求则越来越大,基于核心竞争力所需要的专业知识需求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高深知识的消费市场,促使知识进行再生产或扩大生产。在知识生产或研发成本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实现知识消费最大化,则有必要寻求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学生人数的激增,研究人才分散到各个知识生产领域,凭借着各自从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和生产实践经验来为企业经济生产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这样,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生产部门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知识生产合作网络,通过各自分散性的专业知识的生产,促进知识网络的扩散发展,最终实现技术的革新。知识网络的扩散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些专业知识市场服务组织应运而生,他们主要通过对知识符号的分析整合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由不同地点的人们生产的符号、概念、理论、模型和数据,将它们组装成新的知识形式”[6],从而为各种产品和生产过程提供增殖服务。如此一来,全球化知识生产网络的扩散,已延伸到世界各种各样的知识生产机构或研究中心,成为一股牵动跨学科、跨国界、跨文化的全球化动力源。
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知识生产网络的扩散,意味着一流学科建设需要“去中心化”,不受中心组织的限制。“去中心化”并不代表没有核心,而是意味着知识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寻求知识的创新,不再局限于特定的项目或任务上,更多的是需要从知识网络的每一个节点去触发新的问题,从而激励多个学科主体的合作参与,打破学科畛域,实现跨学科协调创新。“只要高等教育机构有能力参与到解决问题的网络中,它们就成为知识网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网络将成为经济和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中心。”[7]知识的分散性生产,促使生产组织纷纷寻求知识的共享与合作,大学必须把握住全球化发展的机遇,通过分享智力资源的优势,最终实现知识组织模式的解构与重组,这也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挑战。
三、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我国学科建设的启示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学科知识的逻辑取向具有新的意义,正倒逼着学科发展变革,这警示我们:学科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其发展变革深刻影响着大学的人才培养,客观上要求大学的学科知识、学科组织、学科研究范式等进行深刻变革,以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内在要求,进而实现大学人才培养持续改进和提升。我国提出一流学科建设,目标是推动高水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前列或行列。我国学科建设必须关注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转变传统学科知识、组织、研究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学科建设的实质与核心,促进大学内涵式发展,推动我国高校真正培养出更多的拔尖优秀人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产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来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
(一)学科知识: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的相互协调
知识生产模式决定了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和任务。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学术使命是学科知识定位的出发点,对知识体系的追求是学科的终极目的,学科遵循“学术使命”,沿着知识的分化与整合方向发展。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如同细胞裂变般开始出现分化,新学科产生,同时伴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