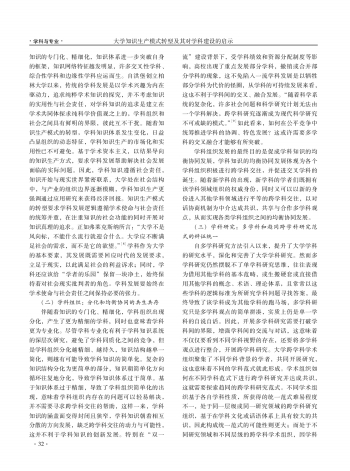知识的专门化、精细化,知识体系进一步突破自身的框架,知识网络特征越发明显,许多交叉性学科、综合性学科和边缘性学科应运而生。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以来,传统的学科发展是以学术兴趣为内在驱动力,追求纯粹学术知识的探究,并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与社会责任,对学科知识的追求是建立在学术共同体探求纯科学价值观之上的,学科组织和社会之间具有鲜明的界限,彼此互不干扰。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学科知识体系发生变化,日益凸显组织的动态特征,学科知识生产的市场化和实用性已不可避免。基于学术资本主义,以结果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要求学科发展帮助解决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学科知识遵循社会责任,知识开始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大学处在社会结构中,与产业的组织边界逐渐模糊,学科知识生产更强调通过应用研究来获得经济回报。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要求学科发展逻辑遵循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的统筹并重,在注重知识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开展对知识真理的追求。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言:“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8]学科作为大学的基本要素,其发展既需要回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立足于现实,以此满足社会的利益诉求;同时,学科还应该给“学者的乐园”保留一块净土,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现实批判者的角色。学科发展要始终在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二)学科组织:分化和均衡协同的共生共存
伴随着知识的专门化、精细化,学科组织出现分化,产生了更为精细的学科,同时也意味着学科更为专业化。尽管学科专业化有利于学科知识系统的深层次研究,避免了学科同质化之间的竞争,但是学科组织分化越精细、越持久,知识结构越单一简化,则越有可能导致学科知识的简单化。复杂的知识结构分化为更简单的部分,知识朝简单化方向循环往复地分化,导致学科知识体系过于简单。基于知识体系过于精细,导致了学科组织简单化的出现,意味着学科组织内存在的问题可以轻易解决,并不需要寻求跨学科交往的帮助,这样一来,学科知识的涵盖面变得封闭且狭窄,学科知识朝着相互分散的方向发展,缺乏跨学科交往的动力与可能性,这并不利于学科知识的创新发展。特别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受学科绩效和资源分配制度等影响,高校出现了重点发展部分学科,撤销或合并部分学科的现象,这不免陷入一流学科发展是以牺牲部分学科为代价的怪圈,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这也不利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发展。“随着科学系统的复杂化,许多社会问题和科学研究计划无法由一个学科解决,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现代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模式。”[9]如此看来,如何在公平竞争中统筹推进学科的协调、特色发展?这或许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才能够有所突破。
学科组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成学科知识的均衡协同发展,学科知识的均衡协同发展体现为各个学科组织积极进行跨学科交往,并促进交叉学科的诞生。随着新学科的出现,新学科的学者们既拥有该学科领域组织的权威身份,同时又可以以新的身份进入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平等的跨学科交往,以对话协商机制为中介达成共识,共享与合作多学科观点,从而实现各类学科组织之间的均衡协同发展。
(三)学科研究:多学科和趋同跨学科研究范式的辩证统一
自多学科研究方法引入以来,提升了大学学科的研究水平,深化和完善了大学学科研究。然而多学科研究仍然摆脱不了单学科研究思维,往往表现为借用其他学科的基本范畴,或生搬硬套或直接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理论体系,且常常以这些学科的逻辑标准为所研究学科问题寻找答案,最终导致了该学科成为其他学科的跑马场,多学科研究只是多学科观点的简单拼凑,实质上仍是单一学科的自说自话。因此,开展多学科研究需要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增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这意味着不仅仅要看到不同学科视野的存在,还要将多学科观点进行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聚集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开展研究,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学科范式就此形成。学术组织如何在不同学科范式下进行跨学科研究并达成共识,这就需要探索趋同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不同学术组织基于各自学科性质,所获得的统一范式难易程度不一,处于同一层级或同一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基于在学科文化或话语体系上具有较大的共识,因此构成统一范式的可能性则更大;而处于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层级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因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