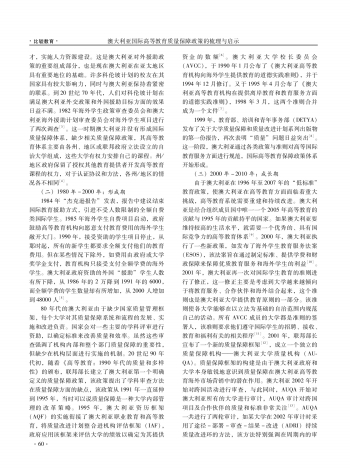才,实施人力资源建设。这是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在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基础。许多科伦坡计划的校友在其国家具有较大影响力,同时与澳大利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科伦坡计划在满足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和外国援助目标方面的效果日益不满。1982年海外学生政策审查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海外援助计划审查委员会对海外学生项目进行了两次调查[3]。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并没有形成国际质量保障体系,缺少相关质量保障政策,其高等教育体系主要由各州、地区或联邦政府立法设立的自治大学组成,这些大学有权力安排自己的课程。州/地区政府保留了授权其他教育提供者开发高等教育课程的权力,对于认证协议和方法,各州/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4]。
(二)1980年-2000年:形成期
1984年“杰克逊报告”发表,报告中建议结束国际教育援助方式,引进不受人数限制的全额自费类国际学生。1985年海外学生自费项目启动,政府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向愿意支付教育费用的海外学生敞开大门。1990年,接受资助的学生项目停止,从那时起,所有的新学生都要求全额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但在某些情况下除外,如费用由政府或大学奖学金支付,教育机构只接受支付全额学费的海外学生。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外国“援助”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从1986年的2万降到1991年的6000,而全额学费的学生数量却有所增加,从2000人增加到48000人[5]。
80年代的澳大利亚由于缺少国家质量管理框架,每个大学对其质量保障系统和流程的发展、实施和改进负责。国家会对一些主要的学科评审进行资助,以确定标准来改善质量和效率。虽然这些审查强调了机构内部和整个部门质量保障的重要性,但缺少在机构层面进行实施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高等教育:1990年代的质量和多样性》的颁布,联邦部长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明确定义的质量保障政策,该政策提出了学科审查方法在质量保障方面的缺点,该政策从1991年一直延伸到1995年,当时可以说质量保障是一种大学内部管理的改革策略。1995年,澳大利亚资历框架(AQF)的实施衔接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将质量改进计划整合进机构评估框架(IAF),政府应用该框架来评估大学的绩效以确定为其提供资金的数额[6]。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AVCC),于1990年1月公布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向海外学生提供教育的道德实践准则》,并于1994年12月修订。又于1995年4月公布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在提供离岸教育和教育服务方面的道德实践准则》,1998年3月,这两个准则合并成为一个文件[7]。
1999年,教育部、培训和青年事务部(DETYA)发布了关于大学质量保障和质量改进计划系列出版物的第一份报告,再次表明“质量”问题日益突出[8]。这一阶段,澳大利亚通过各类政策与准则对高等国际教育服务方面进行规范,国际高等教育保障政策体系开始形成。
(三)2000年-2010年:成长期
由于澳大利亚在1996年至2007年的“低标准”教育政策,使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高等教育系统需要重建和持续改进。澳大利亚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唯一一个2005年高等教育的贡献与1995年的贡献持平的国家。如果澳大利亚要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就需要一个优秀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9]。2000年,澳大利亚执行了一些新政策,如发布了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ESOS),该法案旨在通过制定标准、提供学费和财政保障来保障优质教育服务和海外学生的利益[10]。2001年,澳大利亚再一次对国际学生教育的准则进行了修正,这一修正主要是考虑到大学越来越倾向于将教育服务、合作伙伴和海外结合起来,这个准则也是澳大利亚大学提供教育原则的一部分。该准则使各大学能够在以立法为基础的自治范围内规范自己的活动。所有AVCC成员的大学都是准则的签署人,该准则要求他们遵守国际学生的招聘、接收、教育和福利有关的相关程序[11]。2001年,联邦部长宣布了一个新的质量保障框架[12],成立一个独立的质量保障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机构(AUQA)。质量保障框架的构建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本身敏锐地意识到质量保障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海外市场营销中的潜在作用。澳大利亚2002年开始对跨国活动进行审查,与此同时,AUQA开始对澳大利亚所有的大学进行审计,AUQA审计对跨国项目及合作伙伴的质量和标准非常关注[13]。AUQA一共进行了两轮审计,如某大学在2002年审计时采用了途径-部署-审查-结果-改进(ADRI)持续质量改进环的方法,该方法特别强调在周期内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