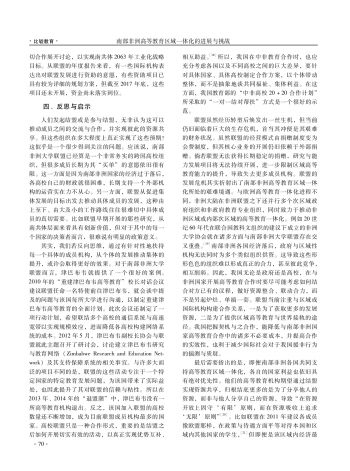切合作展开讨论,以实现南共体2063年工业化战略目标。从联盟的年度报告来看,有一些国际机构表达出对联盟发展进行资助的意愿,有些资助项目已具有较为详细的规划方案,但截至2017年底,这些项目还未开展,资金尚未落实到位。
四、反思与启示
人们发起结盟或是参与结盟,无非认为这可以推动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实现彼此的资源共享。但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这些预期?这似乎是一个很少得到关注的问题。应该说,南部非洲大学联盟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跨国高校组织,但很多成员长期为其“买单”的意愿依旧很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过于落后,各高校自己的财政就很困难,长期支持一个外部机构的运营实在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联盟从促进集体发展的目标出发去推动具体成员的发展,这种由上至下、由大及小的工作路线往往很难切中具体成员的真切需要。比如联盟早期开展的那些研究,从南共体层面来看具有创新价值,但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而言,很难说有明显的政策意义。
其实,我们若反向思维,通过有针对性地扶持每一个具体的成员机构,从个体的发展推动集体的提升,或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对于南部非洲大学联盟而言,津巴布韦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2010年的“重建津巴布韦高等教育”校长对话会议建议联盟任命一名特使前往津巴布韦,就会谈中提及的问题与该国每所大学进行沟通,以制定重建津巴布韦高等教育的全面计划。此次会议还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希望联结多个高校的通信系统与高速宽带以实现规模效应,进而降低各高校构建网络系统的成本。2012年5月,津巴布韦副校长协会与联盟就此主题召开了研讨会,讨论建立津巴布韦研究与教育网络(Zimbabw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及其支持保障系统的相关事宜。与许多大而泛的项目不同的是,联盟的这些活动专注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教育发展问题,为该国带来了实际益处,也因此提升了其对联盟的信赖与粘性。所以在2013年、2014年的“退盟潮”中,津巴布韦没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退出。反之,该国加入联盟的高校数量还不断增加,成为目前联盟成员机构最多的国家。高校联盟只是一种合作形式,重要的是结盟之后如何开展切实有效的活动,以真正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助益。[18]所以,我国在中非教育合作时,也应充分考虑各国以及不同高校之间的巨大差异,要针对具体国家、具体高校制定合作方案,以个体带动整体,而不是抽象地谈共同福祉、集体利益。在这方面,我国教育部的“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所采取的“一对一结对帮扶”方式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联盟虽然经历转型后焕发出一丝生机,但当前仍旧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首当其冲便是其艰难的财务状况。虽然联盟的经营模式由捐赠制度变为会费制度,但其核心业务的开展仍旧依赖于外部捐赠。倘若联盟无法获得长期稳定的捐赠,研究与能力发展项目将无法持续开展,进一步限制区域高等教育能力的提升,导致失去更多成员机构。联盟的发展危机其实折射出了南部非洲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所处的艰难境遇。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不同,非洲大陆在非洲联盟之下还并行多个次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教育专业组织,同时致力于推动非洲区域或内部次区域的高等教育一体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下成立的非洲大学协会就在诸多方面与南部非洲大学联盟存在交叉重叠。[19]南部非洲各国经济落后,政府与区域性机构无法同时为多个类似组织供资。这导致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难以形成真正的合力,甚至彼此竞争,相互削弱。因此,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在与非洲国家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时要尽可能考虑如何结合对方已有的议程,做好资源整合、联动合力,而不是另起炉灶、单搞一套。联盟当前注重与区域或国际机构构建合作关系,一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二是为了提供区域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途径。我国把握契机与之合作,能降低与南部非洲国家高等教育合作中的诸多不必要成本,并提高合作的实效性,也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援非行为的揣测与质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南部非洲各国共同支持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依旧具有绝对优先性。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期望通过结盟实现资源共享,归根结底更多的是为了分享他人的资源,而非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资源,导致 “在资源开放上固守‘有限’原则,而在资源吸收上追求‘无限’原则”[20]。比如联盟在2011年建议各成员像欧盟那样,在政策与待遇方面平等对待本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学生,[21]但即便是该区域内经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