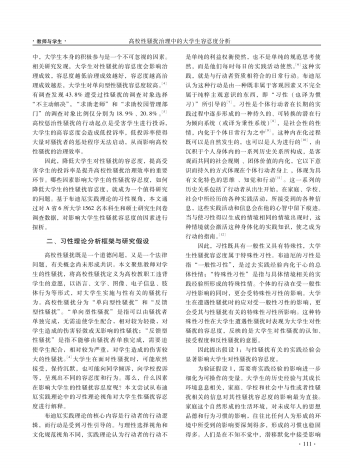中,大学生本身的积极参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会影响治理成效,容忍度越低治理成效越好,容忍度越高治理成效越差,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较高。[4]有调查发现43.8%遭受过性骚扰的调查对象选择“不主动解决”,“求助老师”和“求助校园管理部门”的调查对象比例仅分别为18.9%、20.8%。[5]高校惩治性骚扰的行动起点是受害学生进行投诉,大学生的高容忍度会造成低投诉率,低投诉率使得大量对骚扰者的惩处程序无法启动,从而影响高校性骚扰的治理效率。
因此,降低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提高受害学生的投诉率是提升高校性骚扰治理效率的重要环节。哪些因素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如何降低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习性视角,本文通过对A省6所大学1562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问卷调查数据,对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因素进行探析。
二、习性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高校性骚扰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有关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聚焦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将高校性骚扰定义为高校教职工违背学生的意愿,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大学生实施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高校性骚扰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单向型性骚扰”是指可以由骚扰者单独完成,无需迫使学生配合,相对较为轻微,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轻微或无影响的性骚扰;“反馈型性骚扰”是指不能够由骚扰者单独完成,需要迫使学生配合,相对较为严重,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较大的性骚扰。[4]大学生在面对性骚扰时,可能欣然接受,保持沉默,也可能向同学倾诉,向学校投诉等,呈现出不同的容忍度和行为。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呢?本文尝试从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习性理论视角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进行解释。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行动者的行动逻辑,而行动是受到习性引导的。与理性选择视角和文化规范视角不同,实践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规范思考使然,而是他们每时每日的实践活动使然。[6]这种实践,就是与行动者资质相符合的日常行动。布迪厄认为这种行动是由一种既非属于客观因素又不完全属于纯粹主观意识的东西,即“习性(也译为惯习)”所引导的[7]。习性是个体行动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或译为秉性系统)[8],是社会性的性情,内化于个体日常行为之中[9]。这种内在化过程既可以是自然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为进行的[10],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 、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 ,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 、知觉和行动[11]。这一系列的历史关系包括了行动者从出生开始,在家庭、学校、社会中所经历的各种实践活动,所接受到的各种信息,这些实践活动和信息会在他的心智中留下痕迹。当与使习性得以生成的情境相同的情境出现时,这种情境就会激活这种身体化的实践知识,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12]
·教师与学生·存高校性骚扰治理中的大学生容忍度分析
因此,习性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属于特殊性习性。布迪厄的习性是指“一般性习性”,是过去实践经验内化于心的总体性情;“特殊性习性”是指与具体情境相关的实践经验所形成的特殊性情。个体的行动在受一般性习性影响的同时,更会受特殊性习性的影响。大学生在遭遇性骚扰时的应对受一般性习性的影响,更会受其与性骚扰有关的特殊性习性所影响。这种特殊性习性在大学生遭遇性骚扰时表现为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反映的是大学生对性骚扰的认知、接受程度和反性骚扰的意愿。
因此提出假设1:与性骚扰有关的实践经验会显著影响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
为验证假设1,需要将实践经验的影响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变量。大学生的历史经验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家庭、学校和社会中与性或者性骚扰相关的信息对其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最为直接。家庭这个自然形成的生活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往往比任何人为形成的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形成的习惯也稳固得多。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接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