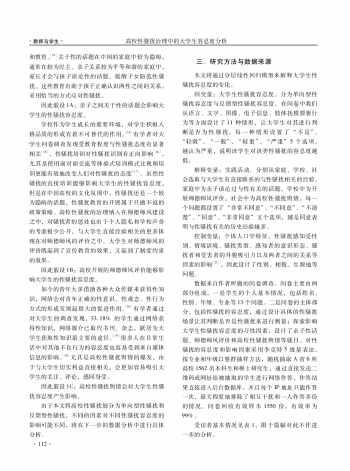和教育。[13]关于性的话题在中国的家庭中较为隐晦,通常在较为民主、亲子关系较为平等和谐的家庭中,家长才会与孩子谈论性的话题,提醒子女防范性骚扰。这些教育有助于孩子正确认识两性之间的关系,采用恰当的方式应对性骚扰。
因此假设1A:亲子之间关于性的话题会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
学校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对学生积极人格品质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4]有学者对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性骚扰态度有显著相关[15],性骚扰培训对性骚扰识别有正向影响[16],尤其是使用面对面交流等体验式培训模式比视频培训更能有效地改变人们对性骚扰的态度[17]。虽然性骚扰的直接培训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但是在中国高校的文化氛围中,性骚扰还是一个较为隐晦的话题,性骚扰教育的开展属于只做不说的政策策略。高校性骚扰的治理纳入在师德师风建设之中,对骚扰者的惩处也由于个人隐私和学校声誉的考虑极少公开,与大学生直接经验相关的更多体现在对师德师风的评价之中。大学生对师德师风的评价既起到了宣传教育的效果,又起到了制度约束的效果。
因此假设1B:高校开展的师德师风评价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
如今的青年大多借助各种大众传媒来获得性知识,网络会对青年正确的性意识、性观念、性行为方式的形成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18]有学者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33.18% 的学生通过网络获得性知识,网络媒介已取代书刊、杂志,跃居为大学生获取性知识最主要的途径。[19]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其他不良行为的容忍度也容易受到来自媒体信息的影响。[20]尤其是高校性骚扰舆情的爆发,由于与大学生切实利益直接相关,会更加容易吸引大学生的关注、评论,感同身受。
因此假设1C:高校性骚扰舆情会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产生影响。
由于本文将高校性骚扰划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可能不同,将在下一步的数据分析中进行具体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来解释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变化。
因变量: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与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在问卷中我们从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抚摸猥亵行为等方面设计了11种情形,让大学生对其进行判断是否为性骚扰,每一种情形设置了“不是”、“轻微”、“一般”、“较重”、“严重”5个选项,越认为严重,说明该学生对该类性骚扰的容忍度越低。
解释变量:实践活动。分别从家庭、学校、社会选取与大学生有直接联系的与性骚扰相关的经验。家庭中为亲子谈论过与性有关的话题,学校中为开展师德师风评价,社会中为高校性骚扰舆情。每一个问题都设置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越是同意表明与性骚扰有关的历史经验越多。
控制变量:个体人口学特征。性骚扰感知受性别、情境语境、骚扰类型、感知者的意识形态、骚扰者和受害者的外貌吸引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21],因此设计了性别、相貌、生源地等问题。
数据来自作者所做的问卷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学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级、专业等13个问题。二是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性骚扰的容忍度,通过设计具体的性骚扰场景让其判断是否是性骚扰来进行测量;探索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习性因素,设计了亲子性话题、师德师风评价和高校性骚扰舆情等题目。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和影响因素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按专业和年级以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A省6所高校1562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通过直接发送二维码或网址给被抽取的学生进行网络作答,作答结果直接进入后台数据库,并且每个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最大程度地排除了相互干扰和一人作答多份的情况。问卷回收有效样本1550份,有效率为99%。
受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限于篇幅对此不作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