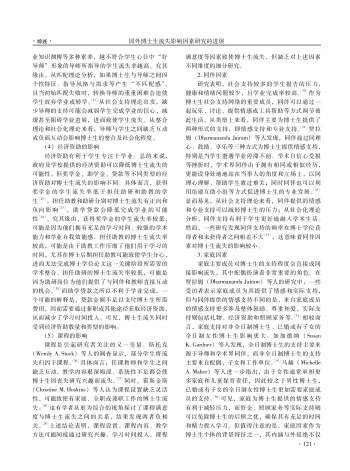业知识渊博等多种素养,越不符合学生心目中“好导师”形象的导师所指导的学生流失率越高。究其缘由,从匹配理论分析,如果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因个性特征、指导风格与需求等产生“不匹配感”,且当初始匹配失败时,转换导师的重重困难会迫使学生放弃学业或转学。[21]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缺少导师的支持可能会减弱学生完成学业的信心,减缓甚至阻碍学业进展,进而致使学生流失。从整合理论和社会化理论来看,导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互动或负面互动会影响博士生的整合及社会化程度。
(4)经济资助的影响
经济资助有利于学生专注于学业。总的来说,政府及学校提供的经济资助可以降低博士生流失的可能性,但奖学金、助学金、贷款等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博士生流失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流失率低于担任助研和助教的学生[22],担任助教和助研分别对博士生流失有正向和负向影响[23],助学贷款会降低完成学业的可能性[24]。究其缘由,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流失率较低,可能是因为他们拥有充足的学习时间、较强的学术能力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担任助教的博士生流失率较高,可能是由于助教工作压缩了他们用于学习的时间,尤其在博士后期担任助教可能致使学生分心,进而无法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这一关键阶段所需要的学术整合。担任助研的博士生流失率较低,可能是因为助研岗位为他们提供了与同伴和教师直接互动的机会。[25]而助学贷款之所以不利于学业完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贷款金额不足以支付博士生所需费用,因而需要通过兼职或其他途径获取经济资助,从而减少了学习时间投入。可见,博士生流失同时受到经济资助数量和类型的影响。
(5)课程的影响
课程是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又一变量。斯托克(Wendy A.Stock)等人的调查显示,部分学生将流失归因于课程。[26]具体而言,任课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教学内容艰深晦涩、系统性不足都会使博士生因丧失研究兴趣而流失。[27]同时,霍斯金斯(Christine M.Hoskins)等人认为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可能致使有家庭、全职或兼职工作的博士生流失。[28]也有学者从更为综合的视角探讨了课程满意度与博士生流失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负相关。[29]上述结论表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可能间接通过研究兴趣、学习时间投入、课程满意度等因素致使博士生流失,但缺乏对上述因素不同维度的细分研究。
2.同伴因素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较多的学生报告的压力、健康和情绪问题较少,且学业完成率较高。[30]作为博士生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成员,同伴可以通过一起玩乐、讨论、提供情感或工具帮助等方式调节彼此生活。从类型上来看,同伴主要为博士生提供了两种形式的支持,即情感支持和专业支持。[31]贾拉姆(Dharmananda Jairam)等人发现,同伴通过同理心、鼓励、享乐等三种方式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支持,特别是当学生遭遇学业停滞不前、学术自信心受损等挫折时,学术界同伴由于拥有相同或相似经历,更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和立场上,以同理心理解、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同时同伴也可以利用组建互助小组等方式促进博士生的专业发展。[32]显而易见,从社会支持理论来看,同伴提供的情感和专业支持可以减轻博士生的压力;从社会化理论分析,同伴支持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学术生活。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同伴支持的频率在博士学位获得者和未获得者之间相差不大[33],这意味着同伴因素对博士生流失的影响较小。
3.家庭因素
家庭主要成员对博士生的支持程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流失,其中配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贾拉姆(Dharmananda Jairam)等人的研究中,一些受访者表示家庭成员为其提供了情感和实际支持,但与同伴提供的情感支持不同的是,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更多涉及整体鼓励、尊重和爱,实际支持则包括礼物、经济资助和照顾家务等。[34]相较而言,家庭支持对非全日制博士生、已婚或有子女的全日制女性博士生影响更大。如加德纳(Susan K.Gardner)等人发现,全日制博士生的支持主要来源于导师和学术界同伴,而非全日制博士生的支持主要来自配偶、子女和工作单位。[35]马赫(Michelle A.Maher)等人进一步指出,由于女性通常承担更多家庭和儿童保育责任,因此较之于男性博士生,已婚或有子女的全日制女性博士生更加需要家庭成员的支持。[36]可见,家庭为博士生提供的情感支持有利于减轻压力,而资金、照顾家务等实际支持则可以免除博士生的后顾之忧,确保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但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因素作为博士生个体的背景特征之一,其内涵与外延绝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