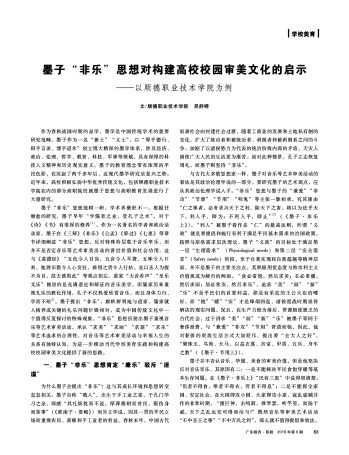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墨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研究范畴。墨子作为一名“兼士”“义士”,以“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创立博大精深的墨学体系,涉及经济、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具有深厚的科技人文精神和历史现实意义。墨子的教育理念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在沉寂了两千多年后,近现代墨学研究呈复兴之势。近年来,高校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部分高职院校就墨子思想与高职教育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
墨子“非乐”思想独树一帜,学术界褒贬不一。根据任继愈的研究,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对于《诗》《书》有很深的修养[1]。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墨子在《三辩》《非乐》《公孟》《辞过》《七患》等章节详细阐述“非乐”思想,反对特殊阶层耽于音乐享乐,而并不是否定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的普世价值和社会功用,这与《道德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等观点相左。道家“大音希声”“至乐无乐”推崇的是充满道论和辩证的音乐美学,而儒家历来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孔子不仅热爱欣赏音乐,而且身体力行、学而不殆①。墨子提出“非乐”,旗帜鲜明地与道家、儒家就人格养成关键的礼乐问题针锋相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值得反复探讨的特殊现象。“非乐”思想折射出墨子重视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承认“求美”“求丽”“求新”“求乐”等艺术追求的合理性,对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与幸福人生的关系有独特认知,为进一步推动当代学校美育实践和构建高校校园审美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墨子“非乐”思想肯定“康乐”驳斥“淫溢”
为什么墨子会提出“非乐”?这与其成长环境和思想转变息息相关。墨子自称“贱人”,出生于手工业之家,于孔门学习之余,深感“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身而害事”(《淮南子·要略》)而另立学说,因其一贯的平民立场而重视农民、商贩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春秋末年,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制的变化,扩大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加剧了以诸侯势力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更为凄苦。面对此种情景,孔子立志恢复周礼,而墨子则坚持“非乐”。
与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墨子对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的看法是其政治伦理学说的一部分,要研究墨子的艺术观点,应从其政治伦理学说入手。“非乐”思想与墨子的“兼爱”“非攻”“节葬”“节用”“明鬼”等主张一脉相承,究其缘由“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2](《墨子·非乐上》)。“利人”被墨子看作是“仁”的最高法则,所谓“义政”就是要提倡和施行有利于满足平民基本需求的治国政策。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墨子“义政”的目标处于满足第一层“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和第二层“安全需求”(Safety needs)阶段,至于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等精神层面,并不是墨子的主要关注点,其积极用世态度与惟功利主义价值观成为硬币的两面。“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追求“美”“丽”“新”“乐”不是平民们的首要利益,那是有采邑的王公大臣的嗜好,而“饱”“暖”“安”才是烽烟四起、诸侯混战时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况且,在生产力较为落后、资源极度匮乏的古代社会,过于讲求“美”“丽”“新”“乐”被墨子等同于奢侈浪费,与“兼爱”“非攻”“节用”背道而驰,因此,他对奢侈的贵族生活方式大加贬斥,提出要“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墨子·节用上》)。
墨子并不否认音乐、华服、美食的审美价值,但是他坚决反对音乐享乐,其原因有二:一是不能解决平民食饱穿暖等基本生存问题。在《墨子·非乐上》“民有三患”中说得很清楚:“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二是不能保全家国、安定社会。在大国即攻小国、大家即攻小家、寇乱盗贼并作的非常时期,“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安可得而治与?”既然音乐等审美艺术活动“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那么就不值得提倡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