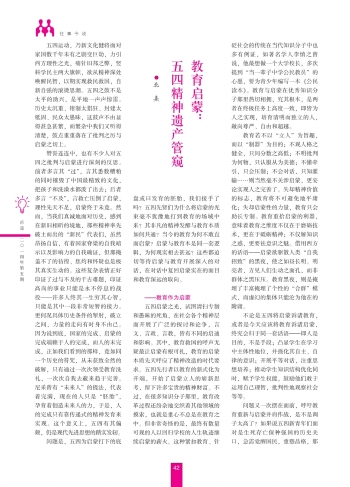五四运动,乃新文化健将面对家国数千年未有之剧变巨劫,力引西方理性之光,痛针旧邦之弊,竖科学民主两大旗帜,欲从精神深处唤醒民智,以期实现救民救国,自新自强的滚烫思潮。五四之鼓不是太平的助兴,是平地一声声惊雷。历史太沉重、钳制太猖狂、封建太柢固、民众太愚昧,这鼓声不由显得甚急甚繁,而繁杂中我们又听得清楚,鼓点重重落在了批判之厉与启蒙之切上。
赞誉连连中,也有不少人对五四之批判与启蒙进行深刻的反思。前者多言其“过”,言其悉数糟粕的同时摧毁了中国最精致的文化,把孩子和洗澡水都泼了出去;后者多言“不及”,言救亡压倒了启蒙,理性先天不足,启蒙终于未竟。然而,当我们真诚地面对历史,感到在新旧相斫的境地,那些精神率先破土而出的“新民”代表们,虽然昂扬自信,有着国家脊梁的自我暗示以及影响力的自我确证,但那掩盖不了的彷徨、焦灼和怀疑也是极其真实生动的。这些复杂表情正好印证了过与不及的千古难题,印证高尚的事业只能是永不停息的战役——许多人终其一生穷其心智,只能是其中一段非常短暂的接力。更何况具体历史条件的掣肘,破立之间,力量的走向有时身不由己。因为说到底,国家的完成、启蒙的完成端赖于人的完成,而人的未完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竟如同一个历史的符咒,从未获致全然的破解,只有通过一次次领受教育洗礼,一次次自我去蔽来趋于完善。尼采曾有“未来人”的提法,代表着完满,现在的人只是“胚胎”,孕育着创造未来人的力,于是,人的完成只有靠传递式的精神发育来实现。这个意义上,五四有其偏颇,仍是现代先进思想的踏实发轫。
问题是,五四为启蒙打下的底盘或曰发育的胚胎,我们接手了吗?五四先贤们为什么将启蒙的光束毫不犹豫地打到教育的场域中来?其非凡的精神发酵与教育本质如何共通?当今的教育为何不敢直面启蒙?启蒙与教育本是同一套逻辑,为何现实相去甚远?这些都迫切等待启蒙与教育开展深入的对话,在对话中复回启蒙实在的面目和教育深远的取向。
——教育作为启蒙
五四启蒙之光,试图清扫专制和愚昧的死角,在社会各个精神层面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和论争,言文、言政、言教,皆有不同的启迪和影响。其中,教育救国的呼声无疑最让启蒙有根可扎,教育的启蒙本质先天呼应了精神改造的时代要求。五四先行者以教育的新式化为开端,开始了启蒙立人的崭新思考,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过,在很多知识分子那里,教育改革过程还纷杂地交织着其他领域的摸索,也就是重心不总是在教育之中。但非常奇怪的是,最终有数量可观的人以回归学校的人生轨迹继续启蒙的薪火。这种紧扣教育、针砭社会的传统在当代知识分子中也多有例证,如著名学人李慎之曾说,他最想做一个大学校长,多次提到“当一辈子中学公民教员”的心愿,要为青少年编写一本《公民读本》。教育与启蒙在优秀知识分子那里热切相拥,究其根本,是两者在终极任务上高度一致,即皆为人之实现,培育清明而独立的人,敞向尊严、自由和超越。
教育若不以“立人”为旨趣,而以“制器”为目的;不观人格之健全,只问分数之高低;不明批判为何物,只认服从为美德;不懂牵引,只会压制;不会对话,只知灌输……则当然毫不关涉启蒙,更妄论实现人之完善了。失却精神价值的标志,教育将不可避免地平庸化;失却启蒙性的力量,教育只会助长专制。教育重拾启蒙的利器,意味着教育之维度不仅在于磨砺技术,更在于砥砺精神;不仅解知识之惑,更要祛意识之魅。借用西方的话语——启蒙欲驱散人类“自我招致”的黑夜,使之如昼长明。明亮者,方见人们生动之面孔,而非群体之黑压压。教育黑夜,则是掩埋了丰富掩埋了个性的“合群”模式,而虚幻的集体只能沦为他在的附庸。
不论是五四将启蒙诉诸教育,或者是今天应该将教育诉诸启蒙,终究会归于同一套话语——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凸显学生在学习中主体性地位,并强化其自主、自律的意识;开展平等对话,注重思想培养;推动学生知识结构优化同时,赋予学生权能,鼓励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理智,批判性地观察社会等等。
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呼吁教育重新与启蒙并肩作战,是不是调子太高了?如果说五四新青年们面对是生死存亡保种强国的历史关口,急需觉醒国民,重塑品格,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