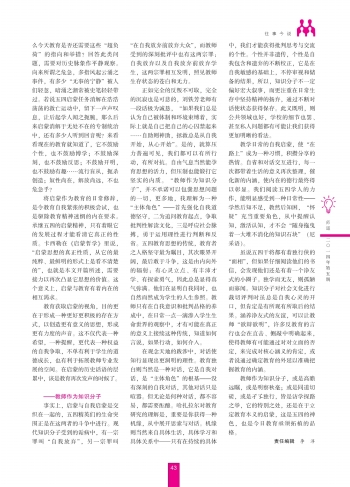将启蒙作为教育的日常修辞,是令教育自我紧张的积极尝试,也是驱除教育精神迷惘的内在要求。承继五四的启蒙精神,只有着眼它的发展过程才能看清它真正的性质。卡西勒在《启蒙哲学》里说,“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也就是本文开篇所述,需要接力以再次凸显它思想的价值。这个意义上,启蒙与教育有着内在的相互渴求。
教育获取启蒙的视角,目的更在于形成一种更好更积极的存在方式,以创造更有意义的思想,形成更有力度的声音。这不仅代表一种希望,一种提醒,更代表一种权益的自我争取,不单有利于学生的道德成长,也有利于拓展教师专业发展的空间。在启蒙的历史话语的层累中,该是教育再次发声的时候了。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事实上,启蒙与自我启蒙是交织在一起的,五四精英们的生命突围正是在这两者的斗争中进行。现代知识分子受到的诟病中,有一宗罪叫“自我放弃”,另一宗罪叫“在自我放弃前放弃大众”,而教师受到的深刻批评中也有这两宗罪:自我放弃以及自我放弃前放弃学生,这两宗罪相互发明,照见教师生存状态的苍白和无力。
正如完全的反叛不可取,完全的沉寂也是可悲的,刘铁芳老师有一段话极为诚恳,“如果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被体制和环境束缚着,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心囚禁起来 ……自助则神助,拯救总是从自我开始,从心开始”。是的,就算压力普遍可见,我们都可以有所行动,有所对抗。自由气息当然能孕育思想的活力,但压制也能锻打它坚实的内质。“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并不承诺可以包囊思想问题的一切,更多地,我理解为一种“主体角色”——首先强化自我道德坚守,二为追问教育起点,争取批判性解读文化,三是呼应社会脉搏,勇于运用理性进行判断和反省。五四教育思想的传统,教育者之人格坚守最为瞩目,其次眼界开阔,最后敢于斗争,这是由内向外的辐射:有心灵立点、有丰沛才学、有探索勇气,因此总是显得真气弥满。他们在显明自我同时,也自然而然成为学生的人生参照。教师只有在自我意识和批判品格的养成中,在日常一点一滴渗入学生生命世界的观察中,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接续这种传统,知道如何言说,如果行动,如何介入。
在观念天地的跋涉中,对话使知行显现出更洞明的理性。教育独白则当然是一种对话,它是自我对话,是“主体角色”的根基——没有深刻的自我对话,其他对话只是喧嚣。但无论是何种对话,都不容易,都需要酝酿。哈扎拉尔对教育研究的理解是,重要是你获得一种机缘,从中展开思索与对话。机缘则当然来自具体生活,具体学习和具体关系中——只有在持续的具体中,我们才能获得批判思考与交流的个性。个性并非遗传,个性是自我包含和遗弃的不断校正,它是在自我敏感的基础上,不停审视和储备的结果,所以,知识分子不一定偏好宏大叙事,而更注重在日常生存中坚持精神的扬弃,通过不断对话使状态获得保存。此义既明,则公共领域也好,学校的细节也罢、甚至私人问题都有可能让我们获得更加明晰的看法。
教学日常的自我启蒙,使“在路上”成为一种习惯,积攒分享的热情。自省和对话交互进行,每一次都带着生活的意义再次整理,催化新的内涵,使内在的德行最终得以彰显。我们阅读五四学人的力作,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日常性——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怀疑”充当重要角色,从中提醒认知,激活认知,才不会“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尼采语)。
虽说五四干将都有着独行侠的“面相”,但如果仔细阅读他们的书信,会发现他们还是有着一个诤友式的小圈子。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进行裁切评判时虽总是自我心灵的开口,但肯定是有所观有所取后的结果。涵养诤友式的友谊,可以让教师“欲辩欲明”,许多反教育的言行也会在直击、侧敲中明确起来,使得教师有可能通过对对立面的否定,来完成对核心涵义的肯定,或者说通过确定教育的外延以准确把握教育的内涵。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或是高瞻远瞩,或是明察秋毫;或是同道切磋,或是孑孓独行,皆是访学探路之举,它的特别之处,还是在于立定教育本义的启蒙,这是五四的神色,也是今日教育亟须拓植的品格。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