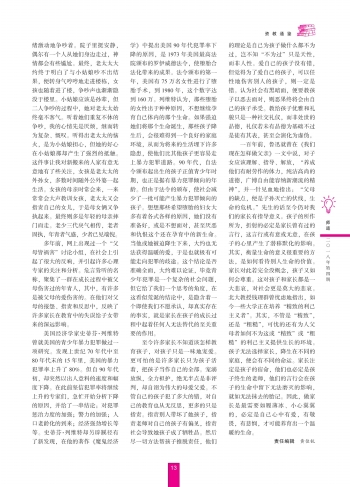多年前,网上出现过一个“父母皆祸害”讨论小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引起许多心理专家的关注和分析。危言耸听的名称,聚集了一群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伤害过的年青人,其中,有许多是被父母的爱伤害的。在他们对父母的报怨、指责和反思中,反映了许多家长在教育中的失误给子女带来的深远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曾就美国的青少年暴力犯罪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上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末的15年里,美国的暴力犯罪率上升了80%。但自90年代初,却突然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幅度下降。在此前坚信犯罪率将继续上升的专家们,急忙开始分析下降的原因,并给了一串结论:对犯罪惩治力度的加强;警力的加强;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经济强劲增长等等。史蒂芬·列维特却另辟蹊径有了新发现,在他的著作《魔鬼经济学》中提出美国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是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罗伊威德法令,使堕胎合法化带来的成果。法令颁布的第一年,美国有75万名女性进行了堕胎手术,到1980年,这个数字达到160万。列维特认为,那些堕胎的女性出于种种原因,不想继续孕育自己体内的那个生命。如果强迫她们将那个生命诞生,那些孩子降生后,会很难得到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从而为将来的生活埋下许多隐患,使他们比其他孩子更容易走上暴力犯罪道路。90年代,自法令颁布起出生的孩子正值青少年时期,也正是据有暴力犯罪倾向的年龄。但由于法令的颁布,使社会减少了一批可能产生暴力犯罪倾向的孩子。想想那些希望堕胎的妇女大多有着各式各样的原因,她们没有准备好,或是不想面对,甚至厌恶和仇恨这个还在孕育中的新生命。当他或她被迫降生下来,大约也无法获得温暖的爱,于是也就极有可能走向犯罪的歧途。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全面,大约难以论证,毕竟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角度,在这看似荒诞的结论中,是隐含着一个即使我们不愿承认,却真实存在的事实,就是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任何人无法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今许多家长不知道该怎样教育孩子,对孩子只是一味地宠爱。更可怕的是许多家长只为孩子活着,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全部。宠溺放纵,全力袒护,绝无半点是非评判,却自诩为伟大的母爱父爱。不管自己的孩子犯了多大的错,对自己的教育也从无反思,更多的只是指责。指责别人带坏了她孩子,指责老师对自己的孩子有偏见,指责社会导致她孩子成了牺牲品。然后尽一切方法帮孩子推脱责任,他们的理论是自己为孩子做什么都不为过,岂不知“不为过”只是天性,而非人性。爱自己的孩子没有错,但觉得为了爱自己的孩子,可以任性地伤害别人的孩子,则一定是错。认为社会有黑暗面,便要教孩子以恶去面对,则恶果终将会由自己的孩子承受。教给孩子优雅和礼貌只是一种社交礼仪,而非处世的品德,礼仪若未有品德为基础不过是徒有其表,甚至会演化为虚伪。
一百年前,鲁迅就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对子女应该理解、指导、解放,“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先生的话至今仍对我们的家长有指导意义。孩子的所作所为,折射的必定是家长曾有过的言行,这言行或有意或无意,在孩子的心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衡量生命的意义很重要的方法,是如何看待别人生命的价值。家长对此若完全没概念,孩子又如何会尊重。这对孩子和家长都是一大悲哀,对社会更是莫大的悲哀。北大教授钱理群曾忧虑地指出,如今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不管是“精致”,还是“粗糙”,可忧的还有为人父母者如何不为这或“精致”或“粗糙”的利己主义提供生长的环境。孩子无法选择家长,降生在不同的家庭,便会有不同的命运。家长注定是孩子的宿命,他们也必定是孩子终生的老师,他们的言行会在孩子的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影响,就如无法抹去的胎记。因此,做家长是最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必定是自己心中有爱,有敬畏,有悲悯,才可能养育出一个温暖的生命。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