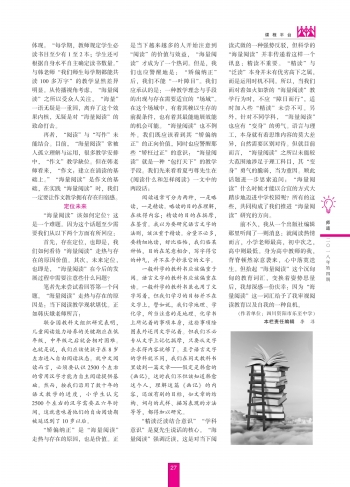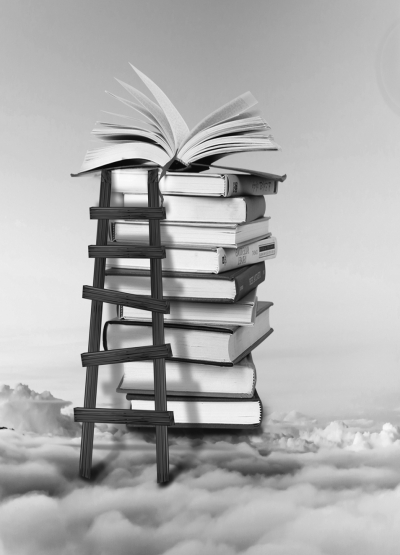再者,“阅读”与“写作”未能结合。目前,“海量阅读”常被人孤立理解与运用,很多教学安排中,“作文”教学缺位。但在韩老师看来,“作文:建立在诵读的基础上。”“海量阅读”是作文的基础,在实践“海量阅读”时,我们一定要让作文教学拥有存在归宿感。
定位未来
“海量阅读”该如何定位?这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个话题至少需要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回应:
首先,存在定位,也即是,我们如何看待“海量阅读”走热与存在的原因价值。其次,未来定位,也即是,“海量阅读”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笔者先来尝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海量阅读”走热与存在的原因是:当下阅读教学现状堪忧。正如韩庆娥老师所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表明,儿童阅读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应在低年级,中年级之后就会相对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使孩子在8岁左右进入自由阅读状态。就中文阅读而言,必须要认识25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才能为自主阅读提供基础。然而,按我们沿用了数十年的语文教学的进度,小学生认完2500个左右的汉字需要五六年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自由阅读期被延迟到了10岁以后。
“矫偏纳正”是“海量阅读”走热与存在的原因,也是价值。正是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阅读”的价值与效益,“海量阅读”才成为了一个热词。但是,我们也应警醒地是:“矫偏纳正”后,我们不能“一叶障目”。我们应承认的是:一种教学理念与手段的出现与存在需要适宜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有着其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有着其最能施展效能的机会可能。“海量阅读”也不例外。我们既应该看到其“矫偏纳正”的正向价值,同时也应警醒那些“矫枉过正”的意识:“海量阅读”就是一种“包打天下”的教学手段。我们先来看看夏丏尊先生在《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一文中的两段话:
阅读通常可分为两种,一是略读,一是精读。略读的目的在理解,在收得内容;精读的目的在揣摩,在鉴赏。我以为要研究语言文字的法则,该注重于精读。分量不必多,要精细地读,好比临帖,我们临某种帖,目的在笔意相合,写字得它的神气,并不在乎抄录它的文字。
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该偏重于阅。语言文字的教科书应该偏重在读。一般科学的教科书虽也用了文字写着,但我们学习的目标并不在文字上,譬如说,我们学地理、学化学,所当注意的是地理、化学书上所记着的事项本身,这些事项除图表外还用文字记着。但我们不必专从文字上记忆揣摩,只要从文字去求得内容就够了。至于语言文字的学科就不同,我们在同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文章——假定是韩愈的《画记》,这时我们不但该知道韩愈这个人,理解这篇《画记》的内容,还该有别的目标,如文章的结构、词句的式样、描写表现的方法等等,都得加以研究。
“精读泛读结合意识”“学科意识”是夏先生说话的核心。“海量阅读”强调泛读,这是对当下阅读式微的一种强势反驳,但科学的“海量阅读”并非传递着这样一个讯息:精读不重要。“精读”与“泛读”本身并未有优劣高下之属,而是运用时机不同。所以,当我们面对着如火如荼的“海量阅读”教学行为时,不应“障目而行”,适时加入些“精读”未尝不可。另外,针对不同学科,“海量阅读”也应有“变身”的勇气。语言与理工,本身就有着思维内容的莫大差异,自然需要区别对待。但就目前而言,“海量阅读”之所以未能较大范围地涉足于理工科目,其“变身”勇气的脆弱,当为重因。顺此话题进一步思索追问:“海量阅读”什么时候才能以合宜的方式大踏步地迈进中学校园呢?所有的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推进“海量阅读”研究的方向。
前不久,我从一个出版社编辑那里听闻了一则消息:就阅读热情而言,小学老师最高,初中次之,高中则最低。身为高中教师的我,背脊顿然凉意袭来,心中落寞迭生。但拾起“海量阅读”这个沉甸甸的教育词汇,变换着姿势思量后,我却深感一份庆幸:因为“海量阅读”这一词汇给予了我审视阅读教育以及自我的一种良机。
(作者单位:四川资阳市乐至中学)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