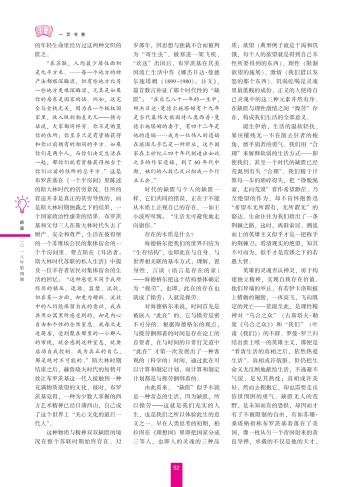“在苏联,人均最少居住面积是九平方米。……每一个地方的财产法都艰深晦涩,但有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艰深晦涩,尤其是如果你的房东是国家的话。例如,这完全与金钱无关,因为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收入级别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大家都同样穷。你不是购置你的住所:你至多只是有资格获得和你以前拥有的相同的平方。如果你们是两个人,而你们决定生活在一起,那你们就有资格获得相当于你们以前的住所的总平方。”这是布罗茨基在《一个半房间》里陈述的斯大林时代的贫穷景况。住所的窘迫并非是真正的贫穷导致的,而是斯大林时期独裁之下的结果,一个国家政治性虚荣的结果。布罗茨基和父母三人在斯大林时代失去了财产、安全和尊严,生活在彼得堡的一个苏维埃公民的集体宿舍的一个半房间里。费吉斯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提及一位幸存者居民对集体宿舍的生活的回忆:“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斯大林时期结束之后,赫鲁晓夫时代的短暂开放让布罗茨基这一代人接触到一种充满物质欲望的文化,彼时,布罗茨基觉得,一种为少数人掌握的西方艺术精神已经日薄西山,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关心文化的最后一代人”。
这种物质与精神双双缺匮的境况在整个苏联时期始终存在。32岁那年,因思想与独裁不合而被判为“寄生虫”、被塞进一架飞机、“欢送”出国后,布罗茨基在其美国流亡生活中作《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篇首数言补证了那个时代性的“缺匮”:“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60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时代的缺匮与个人的缺匮一样,它们共同的错误,正在于不能从本质上正视自己的存在,一如王小波所叹惋:“生活无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海德格尔把我们的世界归结为“生存结构”,也即此在与自身、与世界相关联的基本方式:理解,置身性,言谈(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把这个结构整体确定为“操劳”,也即,此在的存在也就成了操劳:人就是操劳。
对海德格尔来说,时间首先是被嵌入“此在”的,它与操劳是密不可分的。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与操劳捆绑着的时间是存在论上的首要者,在与时间的日常打交道中“此在”才第一次发展出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时间,通过此在可以计算和制定计划,而计算和制定计划都是与操劳捆绑着的。
由此看来,“缺匮”似乎本就是一种常态的生活,因为缺匮,所以操劳——这就是我们充实的人生,也是我们之所以体验此生的意义之一。早在人类思考的初期,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即把国家分成三等人,也即人的灵魂的三种品质:欲望(典型例子就是干渴和饥饿,每个人的欲望就是得到自己本性所要得到的东西)、理性(限制欲望的施展)、激情(我们借以发怒的那个东西)。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正义的人使得自己灵魂中的这三种元素井然有序。在缺匮与理性激情之间“操劳”存在,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诞生伊始,生活的温软轻抚、暴戾摧残无一不在削去狂者的棱角,磨平狷者的勇气。我们用“合理”来解释软弱的生活方式——即使我们、甚至一个时代的缺匮已经荒诞到有失“合理”。我们精于计算每一步的琐碎得失,把“挣脱绳索,走向荒漠”看作希望渺茫、乃至绝望的作为,却不肯怀抱鲁迅“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豁达。生命往往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荆棘之路,这时,离群索居、溯流而上的英雄主义似乎才是一把称手的荆棘刀;看清现实的绝望,知其不可而为,似乎才是荒谬之下的若愚大智。
英雄的灵魂否认神灵,勇于构建独立精神,实现自我存在价值。他们异端的举止,有若伊卡洛斯披上蜡做的翅膀,一再高飞,飞向既定的死亡——荒诞至此,是理性精神对“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和“我们”(叶甫《我们》)的不群。罗曼·罗兰归结出世上唯一的英雄主义,那便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真相或许肮脏,但仍把生命义无反顾地献给生活,不逃避不气馁,足见其热忱;真相或许美好,然而去拥抱它,却也需要走出俗世围困的勇气。缺匮无人的荒野,是未知而有的恐惧,却因而才有了不被限制的自由,有如苏珊·桑塔格指称布罗茨基着落在了美国,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善良导弹,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