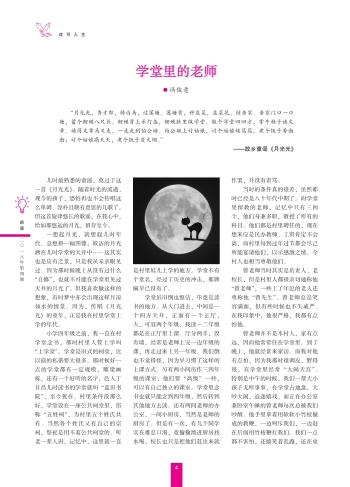“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口一口塘,蓄个鲤蟆八尺长。鲤蟆背上承灯盏,鲤蟆肚里做学堂。做个学堂四四方,掌牛赖子读文章。读得文章马又走,一走走到伯公坳。伯公坳上讨姑娘,讨个姑娘矮笃笃,煮个饭子香勃勃;讨个姑娘高天天,煮个饭子臭火烟。”
——故乡童谣《月光光》
儿时最熟悉的童谣,莫过于这一首《月光光》。随着时光的流逝,现今的孩子,恐怕再也不会传唱这么单调、淳朴且颇有意思的儿歌了。但这首旋律悠长的歌谣,在我心中,恰如那悠远的月光,留存至今。
一想起月光,就想起儿时年代。总想拼一幅图像:皎洁的月光洒在儿时学堂的天井中……这其实也是应有之景,只是我从未亲眼见过。因为那时候晚上从没有过什么“自修”,也就不可能在学堂里见过天井的月光了。但我喜欢做这样的想象,有时梦中亦会出现这样月凉如水的情景。因为,传唱《月光光》的童年,正是我在村里学堂上学的年代。
小学四年级之前,我一直在村学堂念书,那时村里人管上学叫“上学堂”。学堂是旧式的祠堂,比以前的私塾要大很多。那时候好一点的学堂都有一定规模,雕梁画栋,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邑人丁日昌儿时读书的学堂就叫“蓝田书院”,至今犹在。村里条件没那么好,学堂设在一座公共祠堂里,俗称“五姓祠”,为村里五个姓氏共有。当然各个姓氏又有自己的宗祠,祭祀是用不着公共祠堂的。听老一辈人讲,记忆中,这里就一直是村里娃儿上学的地方。学堂本有个堂名,经过了历史的冲击,那牌匾早已没有了。
学堂虽旧倒也整洁,毕竟是读书的地方。从大门进去,中间是一个四方天井,正面有一个正厅,大,可容两个年级,我读一二年级都是在正厅里上课。厅分两半,没有墙,经常是老师上完一边年级的课,再走过来上另一年级。我们倒也不觉得怪,因为早习惯了这样的上课方式。另有两小间房作三四年级的课室,他们要“高级”一些,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课室。学堂里念书也就只能念到四年级,然后转到其他地方去读。还有两间老师的办公室,一间小厨房,当然是老师的厨房了。但是有一次,有几个同学实在难忍口渴,竟偷偷溜进厨房找水喝,校长也只是把他们赶出来就作罢,并没有责骂。
当时的条件真的很差,虽然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而学堂里留教的老师,记忆中只有三四个,他们身兼多职,教授了所有的科目。他们都是村里聘任的,现在想来应是民办教师,工资肯定不会高,而村里每到过年过节都会尽己所能宴请他们,以示感激之情。全村人也相当尊敬他们。
曾老师当时其实是负责人、老校长,但是村里人都很亲切地称他“曾老师”,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尊称他“曾先生”。曾老师总是笑容满面,但有些时候也不失威严。在我印象中,他很严格,我都有点怕他。
曾老师并不是本村人,家有点远,因而他常常住在学堂里。到了晚上,他就经常来家访。而我对他有点怕,因为我那时很调皮,野得很,在学堂里经常“大闹天宫”。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我们一帮大小孩子无所事事,在学堂占地盘,大吵大闹,追逐嬉戏,而正在办公室兼卧室午睡的曾老师每次总被我们吵醒。他手里拿着用软软小竹枝做成的教鞭,一边呵斥我们,一边赶在后面用竹枝鞭打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还嬉笑着乱跑,还在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