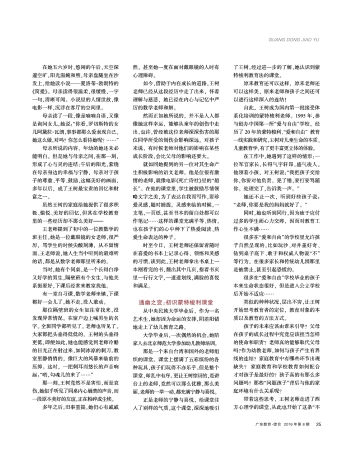母亲读了一段,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询问女儿,她说:“你看,罗切斯特的女儿阿黛拉·瓦朗,事事都那么爱表现自己。她这么做,对吗?你怎么看待她呢?……”
母亲所说的内容,年幼的她还未必能明白。但是她与母亲之间,在那一刻,形成了心与灵的连结:午后的阳光,萦绕在母亲身边的幸福与宁静,母亲对于孩子的尊重、平等、鼓励,这幅美好的画面,多年以后,成了王树最宝贵的回忆和财富之一。
虽然王树的家庭给她提供了很多积极、愉悦、美好的回忆,但其在学校教育里的一些经历却不那么美好——
王老师提到了初中的一位教数学的班主任。她是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很严厉,骂学生的时候尖酸刻薄,从不留情面。王老师说,她人生当中听到的最难听的话,都是从数学老师那里听来的。
当时,她有个同桌,是一个长得白净又好学的男生,隔壁班有个女生,与他关系挺要好,下课后经常来教室找他。
有一堂自习课,数学老师坐镇,下课都好一会儿了,她不走,没人敢动。
那位隔壁班的女生如往常找来,没发现异常情况,在窗户边上喊男生的名字。全班同学都听见了。老师也听见了。大家都把头垂得低低的。王树的头垂得更低,即便如此,她也能感觉到老师冷酷的目光正在射过来,如同冰凉的刺刀。教室里静悄悄的,像巨大的风暴来临前的压抑。这时,一把刺耳而悠长的声音响起:“哟,勾魂儿的来了……”
那一刻,王树竟然不是害怕,而是哀伤,她似乎听见了同桌内心崩溃的声音,而一段原本美好的友谊,正在粉碎成尘埃。
多年之后,旧事重提,她仍心有戚戚然,甚至她一度在面对戴眼镜的人时有心理障碍。
如今,借助于内在成长的道路,王树老师已经从这段经历中走了出来,怀着理解与慈悲,她已经在内心与记忆中严厉的数学老师和解。
然而正如她所说的,并不是人人都像她这样幸运,能够从童年的创伤中走出,也许,曾经被这位老师深深伤害的那位同学所受的创伤会影响深远。对孩子来说,有时候老师对他们的影响在某些成长阶段,会比父母的影响还要大。
就如同她提到的另一位对其生命产生积极影响的语文老师。他是位很有激情的老师,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的“船长”。在他的课堂里,学生被鼓励尽情领略文字之美,为了表达自我而写作,要珍爱灵感,随时捕捉。灵感来临的时候,一支笔,一页纸,甚至书本的留白处都可以作笔记……这样的课堂充满平等、热情,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热爱阅读、热爱生命表达的种子。
时至今日,王树老师还保留着随时在喜爱的书本上记录心得、领悟和灵感的习惯。谈到此,王树老师拿出书桌上一本刚看完的书,翻出其中几页,指着书页里一行行文字,一道道划线,满脸的喜悦和满足。
通幽之变:初识蒙特梭利课堂
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作为一名艺术生,她却因为命运的安排,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幼儿教育之路。
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陪家人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幼儿教师培训。
那是一个来自台湾和国外的老师组织的课堂。课堂上摆满了五彩缤纷的各种玩具,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但是整个课堂,却乱中有序。更让王树惊讶的,是讲台上的老师,竟然可以那么优雅,那么美丽,老师的一举一动,都充满宁静与喜悦。
正是老师的宁静与喜悦,给课堂注入了别样的气质。这个课堂,深深地吸引了王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她认识到蒙特梭利教育法的课堂。
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原来老师还可以这样美,原来老师和孩子之间还可以进行这样深入的连结!
自此,王树成为国内第一批接受体系化培训的蒙特梭利老师。1995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爱与自由”学校。经历了20年的蒙特梭利、“爱和自由”教育一线实践和研究,王树对儿童生命的本质、儿童教育学,有了更丰富更立体的体验。
在工作中,她遇到了这样的情形:一位军官家长,长得气宇轩昂,盛气凌人。他领着小孩,对王树说:“我把孩子交给你,你要对他负责。犯了错,要打要骂随你。处理完了,告诉我一声。”
她还不止一次,听到好些孩子说:“老师,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同时,她也听到同行,因为疲于应付过多的学生而心力交瘁,因而对教育工作心生不满……
很多在“爱和自由”的学校里允许孩子自然呈现的,比如玩沙、对井盖好奇、钻到桌子底下、敢于和权威人物说“不”等行为,在很多家长和传统幼儿园那里是被禁止,甚至引起恐慌的。
很多在“爱和自由”学校毕业的孩子本来生命状态很好,但是进入公立学校后开始不适应……
类似的种种状况,层出不穷,让王树开始思考教育者的定位,教育对象的本质以及教育的方法方式。
孩子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引导?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究竟应该担当怎样的使命和职责?老师真的能够取代父母吗?作为幼教老师,如何与孩子产生有界线的连结?家庭教育中有哪些环节出现缺失?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配合才对孩子是最好的?孩子真的有那么多问题吗?那些“问题孩子”背后与他的家庭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些思考,王树老师走进了西方心理学的课堂,从此也开始了这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