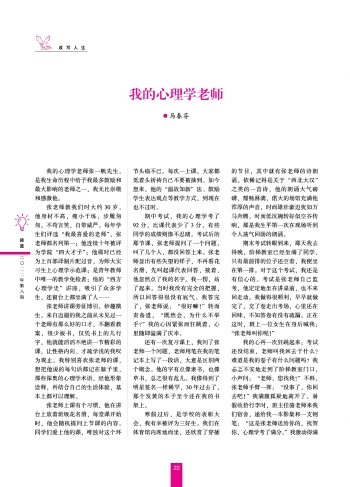■ 马春芬
我的心理学老师张一帆先生,是我生命历程中给予我最多鼓励和最大影响的老师之一,我无比崇敬和感激他。
张老师教我们时大约30岁,他身材不高,瘦小干练,步履匆匆,不苟言笑,自带威严。每年学生们评选“我最喜爱的老师”,张老师都名列第一;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学院“四大才子”;他那时已经为上百部译制片配过音,为师大实习生上心理学示范课;是青年教师中唯一的教学免检者;他的“西方心理学史”讲座,吸引了众多学生,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张老师讲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来自边疆的我之前从未见过一个老师有那么好的口才,不翻看教案,很少板书,仅凭书上的几行字,他就能滔滔不绝讲一节精彩的课,让性格内向、才疏学浅的我叹为观止。我特别喜欢张老师的课,想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记在脑子里,那些深奥的心理学术语,经他形象诠释,再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基本上都可以理解。
张老师上课有个习惯,他在讲台上放着班级花名册,每堂课开始时,他会随机提问上节课的内容。同学们爱上他的课,唯独对这个环节头痛不已。每次一上课,大家都低着头祈祷自己不要被抽到。如今想来,他的“温故知新”法、鼓励学生表达观点等教学方式,到现在也不过时。
期中考试,我的心理学考了92分,比课代表少了3分,有些同学的成绩则惨不忍睹。考试后的那节课,张老师提问了一个问题,叫了几个人,都没回答上来。张老师显出有些失望的样子,不再看花名册,先叫起课代表回答,接着,他忽然点了我的名字。我一愣,站了起来。当时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回答得很没有底气。我答完了,张老师说:“很好嘛!”转而责备道,“既然会,为什么不举手?”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着,心里随即溢满了庆幸。
还有一次复习课上,我问了张老师一个问题,老师用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区别两个概念。他的字有点像隶书,也像草书,总之很有范儿。我像得到了明星签名一样稀罕,30年过去了,那个发黄的本子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
寒假过后,是学校的表彰大会,我有幸被评为三好生。我们在体育馆内席地而坐,还欣赏了穿插的节目,其中就有张老师的诗朗诵。依稀记得是关于“西北大汉”之类的一首诗,他的朗诵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偌大的场馆充满他浑厚的声音,时而雄壮豪迈犹如万马奔腾,时而低沉婉转好似空谷传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场听到令人荡气回肠的朗诵。
期末考试转眼到来,那天我去得晚,阶梯教室已经坐满了同学,只有最前排的位子还空着,我便坐在第一排。对于这个考试,我还是有信心的。考试是张老师自己监考,他定定地坐在讲桌前,也不来回走动。我做得很顺利,早早就做完了,交了卷走出考场,心里还在回味,不知答卷有没有疏漏。正在这时,班上一位女生在身后喊我:“张老师叫你呢!”
我的心再一次狂跳起来:考试还没结束,老师叫我回去干什么?难道是我的卷子有什么问题吗?我忐忑不安地走到了阶梯教室门口,小声问:“老师,您找我?”不料,张老师手臂一挥:“没事了,你回去吧!”我满腹狐疑地离开了。暑假收拾行李时,班主任骆老师来我们宿舍,递给我一本影集和一支钢笔:“这是张老师送给你的,祝贺你,心理学考了满分。”我激动得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