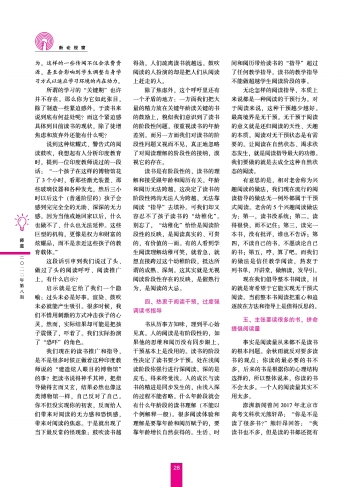为,这样的一些传闻不仅会浪费资源,甚至会影响到学生调整自身学习方式以适应学习环境的内在动力。
所谓的学习的“关键期”也许并不存在。那么你为它如此张目,除了制造一些紧迫感外,于读书来说到底有何益处呢?而这个紧迫感具体到目前读书的现状,除了徒增焦虑和放弃外还能有什么呢?
说到这种炫耀式、警告式的阅读鼓吹,我想起有人分析印度教育时,提到一位印度教师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博物馆花了3个小时,看那些激光装置、那些玻璃仪器和各种发光,然后三小时以后这个(普通阶层的)孩子会感到完完全全的无助、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当他或她回家以后,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无法延伸。这些巨型的机构,更像是权力和财富的炫耀品,而不是亲近这些孩子的教育载体。”
这段话引申到我们说过了头、做过了头的阅读呼吁、阅读推广上,有什么启示?
启示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隐喻:过头未必是好事。渲染、鼓吹未必就能产生吸引。很多时候,我们不惜用刺激的方式冲击孩子的心灵,然而,实际结果却可能是把孩子震慑了,吓着了。我们实际扮演了“恐吓”的角色。
我们现在的读书推广和指导,是不是很多时候正做着这种印度教师说的“建造炫人眼目的博物馆”的事?把读书说得神乎其神,把指导做得玄而又玄,结果必然也像这类博物馆一样,自己反对了自己。你不但没实现你的初衷,反而给人们带来对阅读的无力感和恐惧感,带来对阅读的焦虑。于是就出现了当下最反常的怪现象:鼓吹读书越得劲,人们疏离读书就越远。鼓吹阅读的人扮演的却是把人们从阅读上赶走的人。
除了焦虑外,这个呼吁里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关键年龄读关键的书的鼓励上,貌似我们意识到了读书的阶段性问题,很重视读书的年龄差别。而另一方面我们对读书的阶段性问题又视而不见,真正地忽略了对阅读理解的阶段性的接纳,漠视它的存在。
读书是有阶段性的,读书的理解和接受跟年龄和阅历有关。年龄和阅历无法跨越,这决定了读书的阶段性鸿沟无法人为跨越,无法靠阅读“指导”去填补。可我们却又容忍不了孩子读书的“幼稚化”。别忘了,“幼稚化”恰恰是阅读阶段性的反映,是阅读真实的、可贵的,有价值的一面。有的人看到学生阅读理解幼稚可笑,就着急,就想直接跨过这个幼稚阶段,抵达所谓的成熟、深刻。这其实就是无视阅读阶段性存在的反映,是催熟行为,是阅读的大忌。
四、热衷于阅读干预,过度强调读书指导
书从历事方知味,理到平心始见真。人的阅读是有阶段性的,如果他的思维和阅历没有同步跟上,干预基本上是没用的。读书的阶段性决定了读书要少干预。处在浅阅读阶段你强行进行深阅读,深的是皮毛,得来终觉浅。人的成长与读书的精进是同步发生的,由浅入深的过程不能省略。什么年龄段就会有什么年龄段的读书理解(不能以个例解释一般)。很多阅读体验和理解是要靠年龄和阅历赋予的,要靠年龄增长自然获得的。生活、时间和阅历带给读书的“指导”超过了任何教学指导。读书的教学指导不能做超越学生阅读阶段的事。
无论怎样的阅读指导,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阅读的干预行为。对于阅读来说,这种干预越少越好。最高境界是无干预。无干预于阅读的意义就是还归阅读的天性、天趣的本质。阅读对无干预状态是有需要的。让阅读在自然状态、渴求状态发生,就是阅读指导最大的功德。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成全这种自然状态的阅读。
有意思的是,相对老舍称为兴趣阅读的做法,我们现在流行的阅读指导的做法无一例外都属于干预式阅读。老舍的5个兴趣阅读做法为:第一,读书没系统;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第四,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第五,哼,算了吧。而我们的做法是信任教学阅读,热衷于列书单,开讲堂,做解读,发导引。
现在我们倡导整本书阅读,目的就是寄希望于它能实现无干预式阅读。当前整本书阅读把重心和追逐放在方法和指导上是值得反思的。
五、主张要读很多的书,拼命提倡阅读量
事实是阅读量从来都不是读书的根本问题。余秋雨就反对要多读书的观点:你读的最必要的书不多,后来的书是根据你的心理结构选择的,所以整体说来,你读的书不会太多。一个人的阅读量其实不用太多。
澎湃新闻曾问2017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你是不是读了很多书?”熊轩昂回答:“我读书也不多,但是读的书都还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