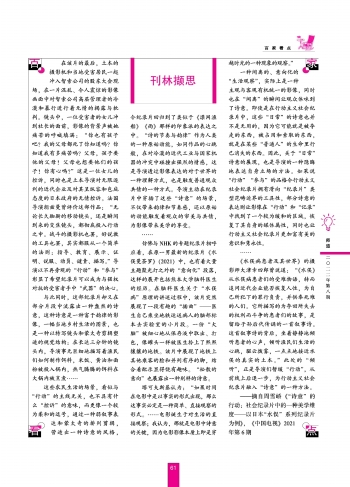在该片的最后,土本的摄影机和当地受害居民一起冲入智索公司的股东大会现场,在一片混乱、令人震惊的影像画面中对智索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冷漠和暴行进行着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镜头中,一位受害者的女儿冲到社长的面前,影像的背景声被她痛苦的呼喊填满:“你也有孩子吧?我的父母都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父母,孩子要他的父母!父母也想要他们的孩子!你有心吗?”这是一位女儿的控诉,同时也是土本导演对无限逐利的近代企业及对其呈纵容和包庇态度的日本政府的无情控诉。法国导演朗兹曼曾评价这部作品:“无论长久踟蹰的移动镜头,还是瞬间到来的变焦镜头,都彻底投入行动之中。战斗的摄影机也罢,好说教的工具也罢,其实都服从一个简单的法则:指导、教育、展示、证明、说服、动员、谴责、描写。”导演以不再旁观的“行动”和“参与”彰显了希望纪录片可以成为与强权对抗的受害者手中“武器”的决心。
与此同时,这部纪录片却又在部分片段中流露出一种盎然的诗意,这种诗意是一种富于韵律的影像,一幅当地乡村生活的图景,也是一种以特写镜头和蒙太奇剪辑塑造的视觉结构:在长达三分钟的镜头内,导演事无巨细地描写着渔民们如何制作饵料,米饭、黄油和面粉被投入锅内,热气腾腾的饵料在大锅内被烹煮……
这些农民生活的场景,看似与“行动”的主线无关,也不具有什么“控诉”的意味,而更像一个较为柔和的逗号,通过一种弱叙事表达和蒙太奇的排列剪辑,营造出一种诗意的风格,令纪录片回归到了类似于《漂网渔船》《雨》那样的印象派的表达之中。“诗的节奏与韵律”作为人类的一种原始动能,如同作品的心跳般,在对冷漠的近代工业与国家机器的冲突中碰撞出强烈的情感,这是导演透过影像表达的对于世界的一种理解方式,也是触发普通观众共情的一种方式。导演主动在纪录片中穿插了这些“诗意”的场景,不仅带来韵律和节奏感,还以原始的动能触发着观众的审美与共情,为影像带来美学的享受。
……
仿佛与NHK的专题纪录片相呼应着,在原一男最新的纪录片《水俣曼荼罗》(2021)中,也有着大量主题聚光灯之外的“意向化”段落,这样的展开包括熊本大学脑科医生的经历。在脑科医生关于“水俣病”原理的讲述过程中,该片突然展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医生自己乘坐地铁运送病人的脑部标本去实验室的小片段。一份“大脑”被细心地从保存液中取出、打包,像罐头一样被医生拎上了熙熙攘攘的地铁。该片中展现了地铁上其他乘客的脸和并列有序的脚,结合着配乐显得饶有趣味。“松散的意向”也展露出一种别样的诗意。
塔可夫斯基认为:“如果时间在电影中是以事实的形式出现,那么这事实必定是一种简单、直接观察的形式。……电影诞生于对生活的直接观察;我认为,那就是电影中诗意的关键,因为电影影像本质上即是穿越时光的一种现象的观察。”
一种间离的、意向化的“生活观察”,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与客观有机统一的影像,同时也在“间离”的瞬间让观众体味到了诗意。即使是在行动主义社会纪录片中,这些“日常”的诗意也并不是无用的,因为它可能就是被夺走的东西,被占用和索取的东西,就是在某些“普通人”的生命里行已消失的东西。因此,关于“日常”诗意的展现,也是导演的一种隐晦地表达自身立场的方法。如果说“行动”“参与”的品格令行动主义社会纪录片拥有滑向“纪录片”类型范畴边界的工具性,部分诗意的表达则让影像在“行动”和“记录”中找到了一个较为缓和的区域,恢复了其自身的媒体属性,同时也让行动主义社会纪录片更加富有美的意识和隽永性。
……
《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的摄影师大津幸四郎曾说道:“《水俣》从水俣病患者们的受难物语,转而追问近代企业能否恢复人性,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并供奉死难的人们。它所描写的为夺回所失去的权利而斗争的患者们的故事,是留给子孙后代传诵的一首叙事诗。这首叙事诗的背后,坐着静静地倾听患者的心声,倾听渔民们生活的心跳,驱云拨雾,一点点地接近水俣的真实的土本。”此处的“倾听”,正是导演们暂缓“行动”,从前线上后退一步,为行动主义社会纪录片融入“诗意”的一种方法。
——摘自周雪峤《“诗意”的行动:社会纪录片中的一种美学维度——以日本“水俣”系列纪录片为例》,《中国电视》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