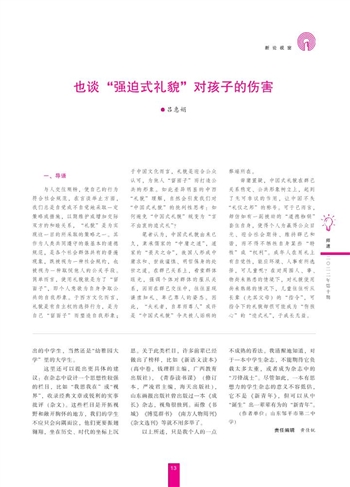■ 吕惠娟
一、导语
与人交往顺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在言谈举止方面,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定策略或措施,以期维护或增加交际双方的和睦关系,“礼貌”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其作为人类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各个社会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既被视为一种社会规约,也被视为一种取悦他人的公关手段。简单而言,使用礼貌就是为了“留面子”,即个人意欲为自身争取公共的自我形象。于西方文化而言,礼貌是有自主权的选择行为,是为自己“留面子”而塑造自我形象;于中国文化而言,礼貌是迎合公众认可,为他人“留面子”而打造公共的形象。如此差异明显的中西“礼貌”理解,自然会引发我们对“中国式礼貌”的批判性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式礼貌”蜕变为“言不由衷的迫式礼”?
笔者认为,中国式礼貌由来已久,秉承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畏天之命”,故国人形成中庸求和、世故谨慎、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在群己关系上,看重群体眼光,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关系,因而在群己交往中,往往显现谦虚知礼、卑己尊人的姿态。因此,“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或许是“中国式礼貌”今天被人诟病的弊端所在。
毋庸置疑,中国式礼貌在群己关系稳定、公共形象树立上,起到了无可非议的作用,让中国不失“礼仪之邦”的称号。可于己而言,却仿如有一副被动的“道德枷锁”套住自身,使得个人为赢得公众目光、迎合社会期待、维持群己和谐,而不得不牺牲自身某些“特性”或“权利”。成年人在用礼上有自觉性,能应环境、人事有所选择,可儿童呢?在对周围人、事、物尚未熟悉的情境下,对礼貌使用尚未熟练的情况下,儿童往往听从长辈(尤其父母)的“指令”,可指令下的礼貌却很可能成为“伤孩心”的“迫式礼”,于成长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