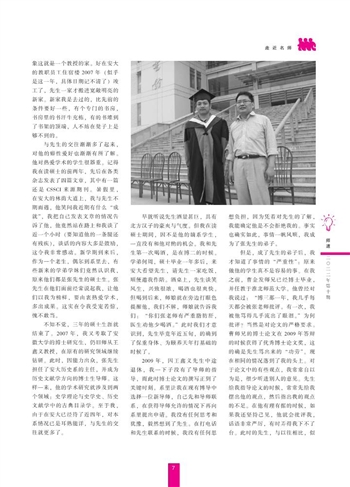象这就是一个教授的家。好在安大的教职员工住宿楼2007年(似乎是这一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竣工了,先生一家才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家。新家我是去过的,比先前的条件要好一些,有个专门的书房,书房里的书汗牛充栋,有的书堆到了书架的顶端,人不站在凳子上是够不到的。
与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对他的癖性爱好也渐渐有所了解。他对热爱学术的学生很器重。记得我在读硕士的前两年,先后在各类杂志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还是CSSCI来源期刊。暑假里,在安大的林荫大道上,我与先生不期而遇,他笑问我近期有什么“成就”,我把自己发表文章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竟然站在路上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要知道他的一条腿还有残疾),谈话的内容大多是鼓励,这令我非常感动。新学期到来后,作为一个老生,偶尔到系里去,有些新来的学弟学妹们竟然认识我,原来他们都是张先生的硕士生。张先生在他们面前经常说起我,让他们以我为榜样,要由衷热爱学术,多出成果。这实在令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
不知不觉,三年的硕士生涯就结束了。2007年,我又考取了安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仍旧师从王鑫义教授,在原有的研究领域继续钻研。此时,因能力出众,张先生担任了安大历史系的主任,并成为历史文献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这样一来,他的学术研究就涉及到两个领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中的古典目录学。至于我,由于在安大已经待了近四年,对本系情况已是耳熟能详,与先生的交往就更多了。
早就听说先生酒量甚巨,具有北方汉子的豪爽与气度。但我在读硕士期间,因不是他的嫡系学生,一直没有和他对酌的机会。我和先生第一次喝酒,是在博二的时候。学弟何周,硕士毕业一年多后,来安大看望先生,请先生一家吃饭,顺便邀我作陪。酒桌上,先生谈笑风生,兴致很浓,喝酒也很爽快。但喝到后来,师娘就在旁边打眼色提醒他,我们不解,师娘就告诉我们:“你们张老师有严重脂肪肝,医生劝他少喝酒。”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先生毕竟年近五旬,的确到了保重身体、为颐养天年打基础的时候了。
2009年,因王鑫义先生中途退休,我一下子没有了导师的指导,而此时博士论文的撰写正到了关键时刻。系里让我在现有博导中选择一位新导师,自己先和导师联系,在获得导师允许的情况下再向系里提出申请。我没有任何思考和犹豫,毅然想到了先生。在打电话和先生联系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因为凭着对先生的了解,我能确定他是不会拒绝我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事情一帆风顺,我成为了张先生的弟子。
但是,成了先生的弟子后,我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原来做他的学生真不是容易的事。在我之前,曹金发师兄已经博士毕业,并任教于淮北师范大学。他曾经对我说过:“博三那一年,我几乎每天都会被张老师批评。有一次,我被他骂得几乎流出了眼泪。”为何批评?当然是对论文的严格要求。曹师兄的博士论文在2009年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奖,这的确是先生骂出来的“功劳”。现在相同的情况落到了我的头上。对于论文中的有些观点,我常常自以为是,很少听进别人的意见。先生给我指导论文的时候,常常先给我摆出他的观点,然后指出我的观点的不足。在他有理有据的时候,如果我还坚持己见,他就会批评我,话语非常严厉,有时弄得我下不了台。此时的先生,与以往相比,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