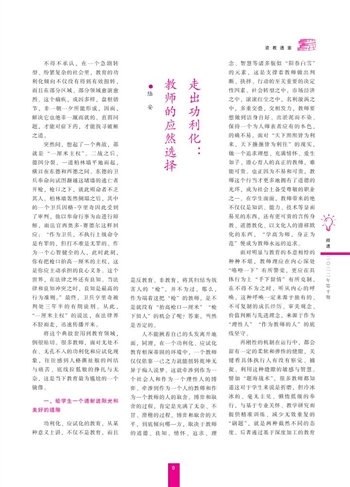■ 陆 安
不得不承认,在一个急剧转型、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扭转,而且在部分区域、部分领域愈演愈烈。这个痼疾,成因多样,盘根错节,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因而,解决它也绝非一蹴而就的。直面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找寻破解之道。
突然间,想起了一个典故,那就是“一厘米主权”。二战之后,德国分裂,一道柏林墙平地而起,横亘在东德和西德之间。东德的卫兵奉命向试图翻越这堵墙的逃亡者开枪,枪口之下,就此殒命者不乏其人。柏林墙轰然倒塌之后,其中的一个卫兵因格·亨里奇因此受到了审判,他以奉命行事为由进行辩解,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这样回应:“作为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最终,卫兵亨里奇被判处三年半的有期徒刑。从此,“一厘米主权”的说法,在法律界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
将这个典故套用到教育领域,倒很贴切。很多教师,面对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功利化和应试化现象,往往感到人格撕扯般的纠结与痛苦、底线拉低般的挣扎与无奈,这是当下教育最为尴尬的一个镜像。
一、给学生一个透射进阳光和美好的缝隙
功利化、应试化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不是教育,而且是反教育、非教育,将其归结为戕害人的“枪”,并不为过。那么,作为端着这把“枪”的教师,是不是就没有“抬高枪口一厘米”“枪下留人”的机会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同理,在一个功利化、应试化教育根深蒂固的环境中,一个教师仅仅依靠一己之力就能扭转乾坤无异于痴人说梦。这就牵涉到作为一个社会人和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博弈、牵涉到作为一个人的教师和作为一个教师的人的取舍。博弈和取舍的过程,肯定是充满了无奈、不甘、滑稽的过程。博弈和取舍的天平,到底倾向哪一方,取决于教师的道德、良知、情怀、追求、理念、智慧等诸多貌似“阳春白雪”的元素,这是支撑着教师做出判断、抉择、行动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社会转型之中,市场经济之中,滚滚红尘之中,名利漩涡之中,多重交叠,交相发力,教师要想做到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一个为人师表者应有的本色,的确不易。面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做一个追求理想、充满情怀、爱生如子、潜心育人的真正的教师,难能可贵。也正因为不易和可贵,教师这个行当才更多地拥有了道德的光环,成为社会上备受尊敬的职业之一。在学生面前,教师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知识、能力、技术等显而易见的东西,还有更可贵的言传身教、道德教化、以文化人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便成为教师永远的追求。
面对明显与教育的本意相悖的种种不堪,教师理应在内心深处“咯噔一下”有所警觉,更应在具体行为上“手下留情”有所克制,在不得不为之时,听从内心的呼唤。这种呼唤一定来源于独有的、不可复制的成长经历、审美观念、价值判断与先进理念,来源于作为“理性人”“作为教师的人”的底线坚守。
再刚性的机制在运行中,都会留有一定的柔软和弹性的缝隙,关键看具体执行人有没有察觉、捕捉、利用这种缝隙的敏感与智慧。譬如“题海战术”,很多教师都知道这对于学生来说是折磨,但冷冰冰的、毫无主见、懒惰低级的奉行,与基于专业关怀、教学研究而提供精准训练、减少无效重复的“刷题”,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后者通过基于深度加工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