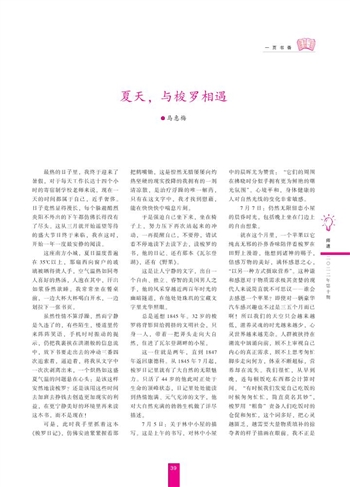■ 马惠梅
最热的日子里,我终于迎来了暑假,对于每天工作长达十四个小时的寄宿制学校老师来说,现在一天的时间都属于自己,近乎奢侈。日子竟然显得漫长,每个躲避酷烈炎阳不外出的下午都仿佛长得没有了尽头。这从三月就开始遥望等待的盛大节日终于来临,我在这时,开始一年一度最安静的阅读。
这座南方小城,夏日温度普遍在35℃以上,那扇西向窗户的玻璃被晒得烫人手,空气温热如同粤人喜好的热汤,人泡在其中,汗出如浆昏然欲睡。我常常坐在餐桌前,一边大杯大杯喝白开水,一边划拉下一张书页。
虽然性情不算浮躁,然而宁静是久违了的,有些陌生,楼道里传来阵阵笑语,手机时时振动的提示,仍把我裹挟在洪潮般的信息流中,放下书要走出去的冲动三番四次追索着,逼迫着,将我从文字中一次次剥离出来,一个炽热如这盛夏气温的问题悬在心头:是该这样安然地读梭罗?还是该用这些时间去加班去挣钱去创造更加现实的利益,在更宁静美好的环境里再来读这本书,而不是现在!
可是,此时我手里抓着这本《梭罗日记》,仿佛安迪紧紧握着那把鹤嘴锄,这是惶然无措屡屡向灼热坚硬的现实投降的我拥有的一剂清凉散,是治疗浮躁的唯一解药,只有在这文字中,我才找到慰藉,能在快快快中喘息片刻。
于是强迫自己坐下来,坐在椅子上,努力压下再次站起来的冲动,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停,请试着不停地读下去读下去,读梭罗的书,他的日记、还有那本《瓦尔登湖》,还有《野果》。
这是让人宁静的文字,出自一个自由、独立、睿智的美国男人之手,他的风采穿越近两百年时光的幽暗隧道,在他处处珠玑的宝藏文字里光华照眼。
总是遥想1845年。32岁的梭罗将背影留给拥挤的文明社会,只身一人,带着一把斧头走向大自然,住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屋。
这一住就是两年,直到1847年返回康德科。从1845年7月起,梭罗日记里就有了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只活了44岁的他此时正处于生命的顶峰状态,日记里处处能读到热情饱满、元气充沛的文字,他对大自然充满的勃勃生机做了详尽描述。
7月5日:关于林中小屋的描写。这是上午的书写,对林中小屋中的晨晖尤为赞赏:“它们的周围在拂晓时分似乎拥有更为鲜艳的曙光氛围”。心境平和,身体健康的人对自然光线的变化非常敏感。
7月7日:仍然无限留恋小屋的晨昏时光,包括晚上坐在门边上的自由想象。
就在这个月里,一个苹果以它纯真无邪的扑鼻香味陪伴着梭罗在田野上漫游,他想到诸神的赐予,倍感万物的美好,满怀感恩之心,“以另一种方式摄取营养”。这种谦和感恩对于物质需求极其贪婪的现代人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谁会去感恩一个苹果?即使对一辆豪华汽车感兴趣也不过是三五个月而已啊!所以我们的天空只会越来越低,滋养灵魂的时光越来越少,心灵世界越来越芜杂。人群被挟持在潮流中汹涌向前,顾不上审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顾不上思考匆忙脚步走向何方,体重不断超标,营养却在流失。我们很忙,从早到晚,连每顿饭吃东西都会计算时间。“有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吃饭的时候匆匆忙忙,简直莫名其妙”,梭罗用“粗鲁”责备人们吃饭时的仓促和匆忙,这个词多好,把心灵越匮乏,越需要大量物质填补的掠夺者的样子描画在眼前。我不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