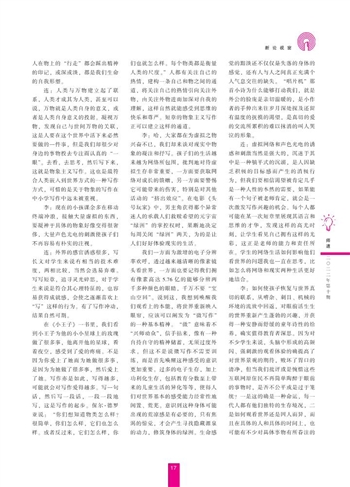人在物上的“行走”都会踩出精神的印记,或深或淡,都是我们生命的自我形塑。
连:人类与万物建立起了联系,人类才成其为人类,甚至可以说,万物就是人类自身的意义,或者是人类自身意义的投射。凝视万物,发现自己与世间万物的关联,这是人要在这个世界中活下来必然要做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却很少对身边的事物投去专注而认真的“一眼”。去看,去思考,然后写下来,这就是物象主义写作。这也是最符合人类嵌入到世界方式的一种写作方式,可惜的是关于物象的写作在中小学写作中远未被重视。
李:现在的小孩课余多在移动终端冲浪,接触大量虚拟的东西,要凝神于具体的物象好像变得很奢侈,大量声色光电的刺激使孩子们不再容易有朴实的注视。
连:外界的感官诱惑很多,写长文对学生来说有相当的技术难度,两相比较,当然会选易弃难。写写短章,追寻灵光碎思,对于学生来说是符合其心理特征的,也容易获得成就感,会使之逐渐喜欢上“写”这样的行为。有了写作冲动,结果自然可期。
在《小王子》一书里,我们看到小王子为他的小小星球上的玫瑰做了很多事,他离开他的星球,看着夜空,感受到了爱的疼痛。不是因为你爱上了她而为她做很多事,是因为为她做了很多事,然后爱上了她。写作亦是如此,写得越多,可能就会对写作爱得越多。写一句话,然后写一段话,一段一段地写,这是写作的起步。保尔·德罗亚说:“你们想知道物类怎么样?很简单,你们怎么样,它们也怎么样。或者反过来,它们怎么样,你们也就怎么样。每个物类都是衡量人类的尺度。”人都有关注自己的热情,建构一条自己和物之间的通道,将关注自己的热情引向关注外物,由关注外物进而加深对自我的理解,这样自然就能感受到思维的快乐和尊严。短章的物象主义写作正可以建立这样的通道。
李:哈,大家都在为虚拟之物兴奋不已,我们却来谈对现实中物象的凝注和抒写。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为网络所包围,批判地对待虚拟生存非常重要,一方面要获取网络对成长的馈赠,另一方面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伤害,特别是对其他活动的“挤出效应”。在电影《头号玩家》中,男主角获得那个异常迷人的承载人们救赎希望的元宇宙“绿洲”的掌控权时,果断地决定每周关闭“绿洲”两天,为的是让人们好好体验现实的生活。
我们一方面为激增的电子分辨率欢呼,透过越来越清晰的像素镜头看世界,一方面也要记得我们拥有像素高达5.76亿的能够分辨两千多种颜色的眼睛,千万不要“宝山空回”。说到这,我想到唤醒我们观看上的本能,将世界重新映入眼帘,应该可以阐发为“微写作”的一种基本精神。“微”意味着不“兴师动众”,信手拈来,像有一种自持自守的精神储蓄,无须过度外求。但这不是说微写作不需要训练,而是首先唤醒这种感受的意识更加重要。过多的电子生存,加上功利化生存,包括教育分数至上带来的儿童生活的异化等等,使得人们对世界基本的感受能力经常性地闲置、荒芜。意识到这种身体可能出现的荒凉感是有必要的,只有焦渴的惊觉,才会产生寻找隐藏源泉的动力,修筑身体的绿洲。生命感觉的黯淡还不仅仅是失落的身体的感觉,还有人与人之间真正充满个人气息交往的缺失。“唱片机”那首小诗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就是外公的脸庞是亲切温暖的,是小作者的手伸出来往岁月深处探及还留有温度的抚摸的渴望,是真切的爱的交流所累积的难以抹消的叫人哭泣的形象。
连:虚拟网络和声色光电的诱惑和刺激当然是强大的,沉迷于其中是一种躺平式的沉溺,是人因缺乏积极的目标感而产生的消极行为,但我们要相信渴望被肯定几乎是一种人性的本然的需要,如果能有一个句子被老师肯定,就会是一次激发写作兴趣的机会。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次短章里展现其语言和思维的才华,发现这样的高光时刻,让学生看见自己拥有这样的光彩,这正是老师的能力和责任所在。学生的网络生活如何影响他们看世界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比如怎么将网络和现实两种生活更好地结合。
李:如何使孩子恢复与世界真切的联系,从嘈杂、刺目、机械的环境的流放中回返,对眼前活生生的世界重新产生蓬勃的兴趣,并获得一种安静而舒缓的童年诗性的给养,确实值得教育者深思。因为对不少学生来说,头脑中形成的高频闪、强刺激的观看体验的确提高了对世界景观的期待,败坏了胃口的清净,但当我们批评或是惋惜这些互联网原住民不再简单陶醉于眼前的事物时,是否不公平或是过于笼统?一是这的确是一种命运,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生存境况,二是如何观看世界还是因人而异,而且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时间上,也可能有不少对具体事物有所眷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