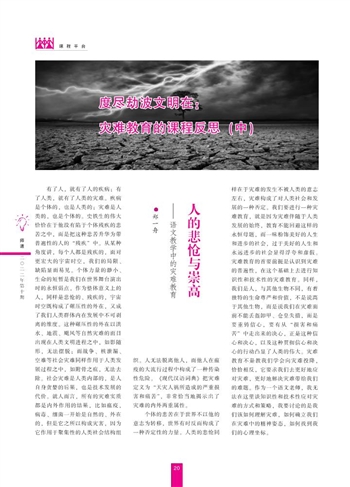■ 郑一舟
有了人,就有了人的疾病;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灾难。疾病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灾难是人类的,也是个体的。史铁生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没有陷于个体残疾的悲苦之中,而是把这种悲苦升华为带普遍性的人的“残疾”中。从某种角度讲,每个人都是残疾的,面对更宏大的宇宙时空,我们的局限、缺陷显而易见。个体力量的渺小、生命的短暂是我们在世界舞台演出时的永恒弱点。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同样是悲怆的、残疾的,宇宙时空既构成了碾压性的外在,又成了我们人类群体内在发展中不可剥离的维度。这种碾压性的外在以洪水、地震、飓风等自然灾难的面目出现在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如影随形,无法摆脱;而战争、核泄漏、空难等社会灾难同样作用于人类发展过程之中,如附骨之疽,无法去除。社会灾难是人类内部的,是人自身贪婪的后果,也是技术发展的代价。就人而言,所有的灾难实质都是内外作用的结果,比如瘟疫,病毒、细菌一开始是自然的、外在的,但是它之所以构成灾害,因为它作用于聚集性的人类社会结构组织。人无法脱离他人,而他人在瘟疫的大流行过程中构成了一种传染性危险。《现代汉语词典》把灾难定义为“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和痛苦”,非常恰当地揭示出了灾难的内外两重属性。
个体的悲苦在于世界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世界有时反而构成了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人类的悲怆同样在于灾难的发生不被人类的意志左右,灾难构成了对人类社会和发展的一种否定。我们要进行一种灾难教育,就是因为灾难伴随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不能回避这样的永恒母题,而一味粉饰美好的人生和进步的社会,过于美好的人生和永远进步的社会显得浮夸和虚假。灾难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认识到灾难的普遍性,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知识性和技术性的灾难教育。同样,我们是人,与其他生物不同,有着独特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不是说高于其他生物,而是说我们在灾难面前不能丢盔卸甲、仓皇失措,而是要重铸信心,要有从“损害和痛苦”中走出来的决心,正是这种信心和决心,以及这种贯彻信心和决心的行动凸显了人类的伟大。灾难教育不是教我们学会向灾难投降,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去更好地应对灾难,更好地解决灾难带给我们的难题。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无法在这里谈知识性和技术性应对灾难的方式和策略,我要讨论的是我们该如何理解灾难,如何确立我们在灾难中的精神姿态,如何找到我们的心理坐标。